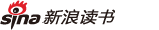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与萧军、端木蕻良合成东北作家群。在短暂、悲苦、充满传奇的一生中,萧红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世俗,历经反叛、觉醒与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一生未向命运低头。作品有《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等。
婚恋史:生为女人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为了求得新知和爱情,萧红决然离家出走,远赴北平。由于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半年之后,她被迫返回老家,最后只好回到未婚夫王恩甲身边。
很快,萧红发现受骗,于是再往北平,试图寻找一种独立的生活。在绝望之际,她与前来营救自己的萧军坠入爱河。1934年6月,二萧逃离“满州国”,南下青岛,继迁上海,过起动荡的流亡生活,他们的家庭出现了可怕的裂痕。萧红继而与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相恋,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但从端木蕻良身上,萧红没有获得她一直渴望的健康和安静的写作环境,感到的只是孤独、失望与无助。
自由和爱情都是萧红所追求的。结果,她死在追求的道路上。她一生所承受的不幸、屈辱和痛苦,至少有一半来自她的“爱人”。
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生活史:贫困体验
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构成为她的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萧红这样被饥饿、寒冷、疾病逼到无可退避的死角而孤立无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性,要具有怎样的自由意志,方可以抵御这一切!
萧红的穷困生活,有过两个严重的阶段:最先是一个人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稍后是同萧军一起生活于商市街。萧红的自叙性散文《商市街》,有多篇文章写到贫穷、饥饿与寒冷,忠实地记录了后一阶段的生活和个人的感受。美国学者葛浩文认为,本书可以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相比拟。
贫困的日子,阴暗的居室,恶劣的环境,永久的焦虑,完全毁坏了萧红的健康。头痛、咳嗽、肚痛、失眠、疲乏……在她此后一生中,这些肺病、胃病、贫血、神经系统的诸多症状从来未曾消失过。
双重视角:穷人与女性
这样,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这两个视角是本体的,本源性的,又是重叠的,复合的。
作为知识女性,萧红虽然不如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那么激烈,直接诉诸于政治行动,但是,在要求男女平等,反对对妇女的歧视、压迫和侮辱,争取妇女的独立自由、自主权利这些方面,她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她没有以传统的伦理观念要求男女的和谐,两性间的一致性,在她看来是只能由“男性中心社会”的瓦解,男性对女性个体的尊重所达致的。所以她认同并赞美妇女对男性的反抗,而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引为耻辱。
但是,萧红看到,在中国社会底层,在农夫农妇中间,他们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急迫的问题,就是生存的权利。在这里,生存高于一切。萧红曾经表示过,男性和女性差异不大,也只是在生存这一层面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她在女性的视域中,多出了一个穷人的视角。这正是萧红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于一般的理念上的女性主义者的地方。
诗性悲剧:自由的风格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萧红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困扰着她,而又促她清醒;无数人的苦难和死亡,不断地震撼着她,召唤她写作。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质性,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
描写世界的衰败与死亡,主题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现代主义意味。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萧红的《呼兰河传》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萧红注重场景切片及细节描写,甚于情节的安排;注重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呈现,甚于性格的刻画。她善于表现人物的孤独、寂寞,人的原子化生存。尤其是后来的小说,表现了她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探询。萧红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萧红的语言肌质是诗性的,抒情、自然而富有弹性。在书写她的乡土故事的时候,除了语言风格自身的美感之外,萧红常常使用省略、跳跃、中断、闪回等多种手段,以加强整体的诗性。她特别注意保留原初的感觉,不去预先设置故事的高潮,任由情节自然发展,随机设喻,通过隐喻和象征扩充了语言的内在张力。
萧红既倾情歌哭社会底层的群体命运,却又执意暴露其中的黑暗和愚昧,而且她是那般恣意地表现自我的个性、思想和情感。而所有这些,是不属于廊庙、山林、经院、书斋、闺阁的,而是属于荒野、泥土的,她流亡、漂泊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在写法上,没有一个小说家像她的那样散文化、诗化,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她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可以认为,她是自弃于主流之外的。除了孤绝的品质,萧红一无所有。
(作者林贤治,根据网络资料选摘,题目为编者所加)
《呼兰河传》选章
萧红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上一篇: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路遥的文学世界
下一篇: 关仁山:我以文学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