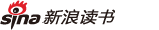聂绀弩的两页奇异诗稿
 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好友张友鸾,写有《聂绀弩诗赠周婆》一文回忆说,早有人劝聂少作诗,“牢骚太盛防肠断”嘛,聂“嘿然无言,似乎接受意见。过几天诗兴又来了,哪里忍得住,头断也不管,何况几寸肠子
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好友张友鸾,写有《聂绀弩诗赠周婆》一文回忆说,早有人劝聂少作诗,“牢骚太盛防肠断”嘛,聂“嘿然无言,似乎接受意见。过几天诗兴又来了,哪里忍得住,头断也不管,何况几寸肠子
聂绀弩真是这样一个“诗痴”、“诗癫”!
自1964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大开展,聂绀弩感受到了政治形势风谲云诡,把自己的诗稿一把火烧了。那一段时间中,他把工夫用在了练习写字上,从“不写诗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演变到了“不写字就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但他骨子里的那种对诗的酷爱不是能够一刀两断的,写字的内容仍然是抄诗,默写他以前作的诗。既要抄写诗,又不能暴露而被祸,这有两全之策吗?亏得他老聂能想得出来。他取了一本线装的旧书,把他的诗用毛笔小楷字,工工整整地写在这本书每一页的左右空白处。这可是既练习了书法,又写了诗,写完把书阖上,鬼才知道有“反动诗”藏在里面。这算是聂绀弩对抗当时政治高压态势的一个锦囊妙计吧!
藏有聂绀弩诗作手迹的这本旧书,叫《蕙?阁诗集》,这是福建刘蘅女士的一部诗集。聂在出版社负责古典文学编辑,手头不乏有此类图书。现在能看到的聂在书页空白处抄写的诗共有26首,都收存于司法档案中。连这样的隐蔽型的手稿都没有能逃脱被搜查的命运,足见当年的“阶级斗争”确是“法网恢恢”残酷无情的。出乎意料的是,恰恰因为搜查而进入了司法档案中,才使诗人的作品得以保存,岂不是坏事变成好事了吗!
到了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聂绀弩本应该“识时务者为俊杰”,完全放下诗笔了;然而,他一面向别人告警,要求人家烧掉他的诗,一面自己却还在写。真是泰山可移,“诗痴”秉性难改啊!当然,他也采取了更加诡异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在八开大小的宣纸块儿上练习小楷书法。写的什么内容呢?写的是毛泽东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等等。但在这些诗句之中,却断断续续夹杂了一些其它文字,写得紊乱不齐,似是随意练习写字。经过仔细观看研究才能发现,把那些错纵零散的文字联缀起来读,就是聂绀弩自己作的诗。
司法案卷中存有两页这样的诗稿。例如,左右两边皆是毛泽东诗词,中间夹着聂绀弩的诗“汝身虽在汝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几十字挤在一起,仔细看才能分辨出来。聂绀弩写的《赠周婆》、《全撕某(胡风)诗稿》等三首诗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夹杂其中的。把自己的诗和毛泽东的诗,掺合书写在一起,佯作练书法状。这当然是诗人为对付风谲云诡的形势,才使用了这样一种奇诡谲异的方法。这些书写稿虽然也被搜抄去了,也入了案卷,却没有当作“反动诗”论处。
现在我们从这奇诡的诗稿中,找出了聂绀弩两首佚诗。这两首诗从内容上看,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写下的。但是,聂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文革”中曾有此类诗作,它们一直就在案卷中默默无闻地沉睡着。因为文字散乱,所以也一直没有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现在我们才从杂乱无章的页面上,把两首诗收拾出来。这也许只是不经意间的戏作,有点“打油”的味道,但除了个别字句以外,总体上还是两首平仄声韵都很严谨的七言律诗。
伤指微签挑不出,
呵创奋帚更挥戈。
无边落木萧萧后,
斗大荒场琐琐多。
牛鬼当前横扫荡,
柴枪棘手小摩挲。
先天早定清除业,
九指畚箕一指螺。
慈亲岳母死还埋,
家谱续修万死该。
三载退休都写稿,
百篇歌颂为贪财。
此真右派枉摘帽,
重扣高冠令扫街。
久在人文出版社,
苍髯老贼张广才。
前一首:扎伤了手的小刺挑不出来,一边呵着伤口,一边又索性奋力挥动起扫帚和武器来。经过狂风暴雨、落叶飘萧之后,就是斗大的一片荒场也暴露出许多卑微的东西来。既然是要“横扫牛鬼蛇神”,手中的枪棒有些棘手就稍稍摩擦一下吧。你这种清剿扫除的事业是先天注定了的,看看你的那手指,十指指纹是九箕一斗啊!(指纹如簸箕状为“箕”,如螺旋状为“斗”。民间有“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开当铺”的谚语,意即“螺斗”是聚敛之兆,“畚箕”有抛除之性。)
后一首:慈亲岳母死了,你还埋葬她,尤其是续修家谱,更是罪该万死的事情。退休了三年都一直在写稿子,写了上百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什么用,让人家说你是贪图稿费、只为发财。你这个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好像白给你摘了帽子,这不又重新扣上一顶高帽子让你去扫大街了。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间很久了,苍白的胡子像《琵琶记》戏中的张广才,怪不得人家批判说你是个“老贼”呢!
这两首诗所指,都应当有具体人具体事,物换星移几十年,当时人物生死两茫然,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我曾就此诗所言及事咨询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人,大都惑惑焉。
前一首写的是造反派。因以前受过微伤而耿耿于怀,趁着大乱的形势挥戈上阵。这人好像是个天生的造反者,指纹有九个簸箕,生就善于簸扬,惟恐天下不乱,惟恐天下富庶,非得折腾个乱、折腾到穷不行。这也许是指某个人,也许是泛指。诗句是叙述、写实,内中却凝结了诗人对那场动乱的愤慨和蔑视。
后一首写的是被批斗的对象。那些诗句其实是借用的大字报、大批判的语言,诗人对这个被批斗者实际是寄予同情的。这个被批斗者是何许人呢?从“退休三年”、“写稿”、“扫街”和“苍髯”这几点看,和张友鸾有些相像之处。至于张友鸾有无埋葬岳母和续修家谱的事,手边无资料可证,所以不敢妄断。
张友鸾(1904-1990),字悠然,著名报人、作家。1953年受聂绀弩之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古典文学。曾被打成“右派”,摘帽后于1962年退休。退休后他主要靠给香港报纸写稿所得稿酬,补充生活消费之需。据舒芜回忆张友鸾的文章(《忆“三同”张老》)中说:“张老‘划右’后工资降了三级,退休还要折扣,本来很窘迫。所幸能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等处开辟专栏,笔耕不已,稿酬以港币计,生活略微宽裕了几年。”“退休后还有一个好处,‘文革’中他没有与我们在职人员一起进牛棚、下干校,只是被‘街道专政’。‘专政’具体内容似乎只是扫胡同……”张友鸾在《胡子的灾难历程》一文中,也曾有这样的回忆:他在扫街时,遇上背照相机的外国人,“慌忙把胡子揣到衣领里,身子缩进了胡同”。
张友鸾早年就留了胡子,到“文革”年代已经成了“白胡子老头”。据他本人回忆说:“‘老家伙’、‘老厌物’、‘老而不死’、‘老奸巨滑’,这都是常听到的叱骂。”这些叱骂语,与聂绀弩诗中的“苍髯老贼”都是同样的意思,都带有那种粗野、蛮横、暴虐的时代色彩。
聂绀弩诗中所写的那个被批斗者,分明是一个他所熟识的人,但诗中没有直接点出此人的姓名,而是用一个戏剧中的人物作了借代。《琵琶记》是南戏的代表性剧目,从上世纪50年代这出戏的上演就成为文学艺术界热烈讨论的议题。聂绀弩专事于古典文学研究,对《琵琶记》的讨论不会不予关注。此剧中的张广才是一个恤邻救难、性善重义的人物,周信芳在京剧折子戏《扫松》中扮演这个角儿,更使其名噪一时。但从偏激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张广才却被批判为封建道德的典型。聂诗中所写的“慈亲岳母死还埋”,本来是通常的孝道,“文革”中也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大加挞伐,正是从这一点上,可以联想到《琵琶记》的批判。剧中人张广才又正好是六十开外的年龄,长着花白胡子,所以聂诗中借取了这个名字。
聂绀弩与张友鸾早年相识,多年共事,友谊甚笃。在聂绀弩诗集中可以看到《悠然五十八》、《悠然六十》等篇什,“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十个字极精彩地概括了张友鸾的情态和人格。现存聂诗中,写张友鸾的诗计有十多首,都是“文革”之前所作,没有“文革”中写的。这次发现的“慈亲岳母死还埋”这首诗,是写于“文革”中的,只是尚不能肯定是写谁,如果真的是写张友鸾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笔调殊异,颇能嚼出一些滋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