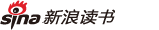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末,当李洁非从文学批评界逐渐疏离,隐身到专题研究上时,并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愈沉潜愈深入、愈庞杂愈开阔的领域。像是一个以笔为武器的斗志昂扬的战士,李洁非突然扛着“枪”转移到后方。后方的战局更为风云叵测,他却以数倍的付出在这里寻到了“战争”的根源。
李洁非选择从小说学开始入手。这是他自80年代后期比较侧重的小说语言、文体批评所延续下来的思路,先写《小说学引论》,然后是《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之后做城市文学研究,出版了该领域较早的研究专著《城市像框》。2003年,他着手延安文学研究,成果就是《解读延安》——这对李洁非而言是比较重要的窗口,从这个研究经历,打开了通向“典型三部曲”的路径。
《典型年度》的出版,为李洁非的“典型三部曲”的出版划上了句号。这部作品选取了新中国后成立六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代,即1956年、1962年、1968年、1972年、1978年、1986年,以年度为横断面,以点带面,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人物和事件放在精神思想史的角度来体察,提供了当代中国的一种思想轨迹。但是很显然,他选择了重要年度,也舍弃了一些重要年度。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典型三部曲”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带来什么?2月22日,李洁非接受本报专访。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您开始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后来转向专项研究,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
李洁非:80年代的文学,思想碰撞激烈。那时我二十四五岁年纪,脑子里还有理想主义,把文学看得蛮高,觉得它如何如何,当时觉得文学病在思想浅薄,认为搞批评比搞创作更有意义,能更直接地介入文学的思想现实。这都是年轻气盛的想法,所谓把思想看重看高,无非是对胸中那些一己之见很在意。到了80年代结束的时候,慢慢觉得执着于个人的东西蛮可笑的,它在现实世界面前分量很轻,根本不足论,与其用主观的想象和规划要求文学,不如脚踏实地研究些问题,认识事实。这样一点一点疏离文学批评前沿,后撤到一些专题的研究上。
读书报:《典型年度》与文学基本无关,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变化的?
李洁非: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可能是这样:虽然《典型年度》很多内容超出文学,但它们并非与文学无关,相反,有千丝万缕联系,甚至在深层真正决定着文学。例如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制度样式、经济形势、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思想价值冲突、领袖人物的治国理念、社会精神视野等等,直接来看都是文学之外的因素,但当代文学六七十年,尤其是前面三四十年历史,大至整个文学走向,小到作品主题、创作方法、风格技巧,究其根源最后都落在这儿,只从文学自身角度解释或者只给以“文学的”解释,根本解释不了。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学“当代性”的本质体现。从文学到文学,既说不清当代文学,更难以说透。这个系列以“典型”命名,含义正在于突显当代文学有非一般的特质,对它的认识,重心应在“当代”两个字,搞懂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现在不少当代文学论文,研究思路与所抱旨趣都一般化,往往从文学的普遍共性着眼,显示不出所研究的是一种形态极为特殊的文学。这种研究称之“文学研究”可以,称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勉强。这样下去,久而久之当代文学究竟怎么回事、它真正面目怎样,会慢慢模糊。
读书报:《典型文坛》对于丁玲、周扬等十一位典型人物的确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典型文案》一书中披露了许多文坛“秘史”,比如郭沫若少年时代的同性恋情结,茅盾退党、入党之谜。在披露这些内容时,您的心里有顾虑吗?您认为这些“秘史”对我们了解作家和作品有帮助吗?
李洁非:人物的数目没有什么含义,目前写了十一位,不表示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只有这十一位,其实还可以沿此思路接着做。关键在于“典型”二字,我内心权衡取舍的依据,就是“当代性”。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历与存在能够比较充分地呈现“当代性”,我认为就够“典型”。过去当代文学史对文学人物的选定,主要看成就高低、知名度、创作地位和作品影响力等,将他们入史作传,意图也主要在于“评价”,从优劣角度提出一些文学史评判。我觉得那是一般文学史眼光或“文学通史”的眼光,不很切中当代文学史特质,对全面反映和说明当代文学史,有相当局限性。所以重要的在于,意识到当代文学史是一段形态极特殊的文学史,我是紧扣于此审视和选择研究对象。
举其中一个例子,为什么写张恨水?因为他是“现代”以来中国畅销文学的代表,而这一写作类型,随着社会历史变更,建国后发生很大变化,实际上是消失了。张恨水活到“文革”前期,他建国后十来年的文学存在,从他本来安身立命的那种文学实践来说,是无效的和失位的。他从一个原创性的畅销小说类型作家变成了依赖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复述者或改编者,虽然仍在写作,其意义只能说是聊以维持一种文字生涯而已。他的这种个人遭遇,绝不止是某个作家自身才华、能力的消长、盛衰而已,而反映出特定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强制性改造和支配,所以是特别有当代文学史意义的现象。再如老舍的例子,建国后老舍较之于从前,文学上可以说判若两人,这种变化,有明显来自外力的作用以及作家迁就、投合或努力适应的动机,也有与他出身背景、地域和阶层文化袭承相一致的东西,非常复杂,而老舍自己在这种迎拒之间也有各种挣扎和徬徨,像大量的曲艺说唱、戏曲脚本、《西望长安》之类与《茶馆》之间,就充满了内心矛盾,尤其是晩期他意态低落时悄悄重拾已搁置多年而最贴合他文学创造性的长篇小说,去写《正红旗下》,以及终于投湖自尽,这样的历程绘呈了一个老作家在“十七年”文学生态下的无尽意味,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由现代入当代的非常好的代际文学状况的典型人物。
《典型文坛》选择人物一个最大特色,我自己认为在于有力突出了文学管理者或文坛领导人这样一个群体,如周扬、丁玲、张光年、郭小川。过去文学史不必考虑这种对象,但当代文学史却必须给他们单独的重视,他们也许不搞创作、不直接投入文学生产,但他们是对文学是给出规则或掌控规则的人,表面上,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实际上作家写作所奉行的规则从他们那儿来,可以说作家写作品而他们则写了作家,这在直到80年代为止的当代文学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当然真正规则制订者并不是这些人,他们作为文学管理者代行代拆而已,但我们通过描述他们、认识他们,无疑可以深入了解当代文学的种种特性。
在做文学史的观察时,我始终不忘记一个“变”字,这个字眼统治了从现代到当代的一切,以及所有人。平常,人习惯于以“后事”概整体,即一个人最后是什么样子,从这一个点上把他认准、认死,而其实每个人都是穿越历史变化而来,所以万万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余。像丁玲和周扬,变化都极大;关于周扬,我就觉得简直有三个周扬,左联的周扬、延安至“十七年”的周扬,“文革”后的周扬,其实哪怕在延安时期,前后周扬也不一样。这种“变”的观点,是我对文学史人物想极力考察的方面,不论是谁,绝不给他一个扁平化、单向度的描述。例如郭沫若,现在的坊议都盯着他建国后尤其是“文革”间的表现,可是他原本性情怎样,他如何崇拜庄子并以自由知识者生存状态为美,这些来历都被疏忽了,您所说的“同性”之好,是他少年时真实经历,应该说那并非他有此性取向,而是一个叛逆性的所谓“顽劣”少年无羁内心所致,这并非“秘史”,而是他亲笔书写在自传里的史实,我写到这些内容也非出于“八卦”目的,是作为对照,来看一个城府颇深、老于世故的人昔年如何自我解放、纯任天成,从而领略社会历史对人的雕刻之力,以及中国知识者在坚持内心方面的普遍的艰困。
读书报:进入文学史的研究,对您自己来说有何影响?在“三部曲”的写作中,您的心态是否也有些变化?能否分享一下写作过程中的艰苦?
李洁非:我在年轻的时候,是颇主观的一个人。做了文学史后得到的最大教益是,论人看事,不要以我为主,什么都从自己出发。里面涉及两个功夫,一是推己及人,一是反求诸己。碰到跟自己思想感情相格不容的人和事,不要代人家立言,把自己放到对象的条件境遇下,找寻他的道理、逻辑。不割裂他,使他自身的联系性完整了。所以主要是心胸,心胸不够,到多大岁数还会极端、主观、绝对。要放下喜厌好恶。喜厌好恶,人之常情,越是常情越要放下。我们不是出于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研究一个人一件事,是为探其由来。所以,即便是反感的、不苟同,也以对象为本位,还原他的心路历程、环境背景。写作中的艰苦,有体力上的,也有心力上的。体力上,穷搜博览还唯恐遗漏,很累。但跟心力的艰苦比,却不算什么。实际上,对写到的人、事和问题,我内心不可能没有臧否,放下喜厌好恶,是将明明有的东西克制住,不让它来干扰研读和写作,这是一个和自我搏斗的过程,碰到我反感甚至憎恶的地方,努力不流露,这是折磨,但没有办法,为着“历史应如镜,勿使惹尘埃”的信念,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