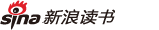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出生于1931年7月10日,加拿大女作家,被称为“加拿大的契科夫”。她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城市度过,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门罗以短篇小说见长,1968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其代表作有《好荫凉之舞》和《逃离》。迄今共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门罗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三次加拿大总督奖、两次吉勒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笔会马拉穆德奖和美国全国书评人奖等。2009年获得第三届布克国际奖。2013年10月10日,艾丽丝•门罗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颁奖词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艾丽丝•门罗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的第13位女性。
读懂艾丽丝·门罗——代表作《逃离》解读
加拿大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是今年掠过我们文学上空的一只大雁。她年纪很大,也写了很多年,只不过咱们中国人见识得晚。
门罗的小说里有一种自然的属性,既亲切、温暖但又让人如临深渊,给了人最有力的启迪。门罗就是这样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她那东拉西扯,充满着朴素观感和触感,淡淡交代的当口,闪烁着明净的智慧。她用一种类似剪纸的方式讲故事,似乎写的都是下脚料、琐屑的事,不成个形状,然而完整读下来,却有着惊人的美丽,而且逻辑上如此严密完整。
短篇小说最重大的特点是陡峭,门罗是平淡至极归于绚烂,这种小说才难写呢,也考验读者的眼力。看似家常,回过味儿来却几乎没有废笔。
门罗的小说里充斥着各种奇迹,在《匆匆》里,牧师唐恩来看望朱丽叶病重的母亲,朱丽叶在大学里主修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一个有妇之夫(他妻子相当于植物人)同居,并生养孩子。唐恩给朱丽叶的第一印象像个推销员,因为朱丽叶不上教堂不给孩子洗礼,两人发生争执。
朱丽叶说,我不相信有神的恩典,我们不想让孩子在谎言中长大。
唐恩说,世界上千百万人都相信了,你称之为谎言,你不是太狂妄了吗?
朱丽叶说,那千百万人不是相信,只是上教堂罢了。而且还有千百万的人相信旁的东西,比如佛。
唐恩说,基督是活的,佛却不是。
朱丽叶让他拿出证据证明哪个是活的,哪个不是。
唐恩说,你知道亨利·福特二世吗,世人想要的一切他都有了,然而他每天晚上跪下来向上帝祷告。
———亨利·福特是汽车大亨。这时候,话题已经变得很俗气了,想想,一个乡村牧师和一个大学高材生,本来就是不对等的关系嘛。情急之中,唐恩的糖尿病发作了,话说不出来,直打抖,朱丽叶给他倒了一杯葡萄汽水喝,这才缓过来。朱丽叶明白了,这是“散兵坑理论”,在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唐恩的病需要信仰支持。
然而,朱丽叶的悲剧没有停步。门罗采用三联剧的方式来写这个知性女孩的命运:《机缘》《匆匆》《沉寂》。三个短篇像三个戏剧片段:《机缘》 写朱丽叶有些生冷的罗曼史;《匆匆》的时钟往后拨了两三年,这时她刚生了孩子,母亲却快死了;《沉寂》则往后推了十几年,朱丽叶的孩子长大成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家出走,彻底抛弃母亲。朱丽叶成了女性的李尔王,年老体衰之年,却遭遇女儿的背叛。这个故事,尽管门罗用波澜不惊的话语描述着一切,不作高声,但非常高明。
门罗的另一大特色是本色。时下流行的小说不是意识形态化,就是形式主义,要不就是集各种学说或学科之大成,小说成了跨界的多媒体,所谓多元化。而门罗成功地摆脱了这一切,有点让小说素面朝天的意思。她完全靠细节、笔触去感知和把握人物。她使故事隐藏在叙事之中,仿
佛老祖母在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语气平淡,然而选择的都是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节点——相逢,相爱,生育,死去,错过……她这本《逃离》全部以女性为主角,清一色的女性视角,一篇一万字的东西常常涵盖了一个女孩悲情的一生。 最重要的,门罗使“女性”由性别而发展成为某种世界观,她们的忍耐、忠贞以及任性和神奇,使世界变得更加丰饶和成熟。
(据《北京日报》)
逃 离
(艾丽丝·门罗)
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那是她呀,她想。是贾米森太太——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了。她站在马厩房门的后面——只是在更靠内里一些的地方,这样就不至于一下子让人瞥见——朝贾米森太太驾车必定会经过的那条路望过去,贾米森太太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和克拉克的家再进去半英里路的地方。
倘若开车的人是准备拐向他们家大门的,车子现在应当减速了。可是卡拉仍然在抱着希望。但愿那不是她呀。
那就是她。贾米森太太的头扭过来了一次,速度很快——她得集中精力才能对付这条让雨水弄得满处是车辙和水坑的砾石路呢——可是她并没有从方向盘上举起一只手来打招呼,她并没有看见卡拉。卡拉瞥见了一只裸到肩部的晒成棕褐色的胳膊,比先前颜色更淡一些的头发——白的多了一些而不是以前的那种银褐色了,还有那副表情,很决断和下了狠劲的样子,却又为自己这么认真而暗自好笑——贾米森太太在跟这样的路况死死纠缠的时候表情总是这样的。在她扭过头来的时候脸上似乎有一瞬间闪了一下亮——是在询问,也是在希望——这使卡拉的身子不禁往后缩了缩。
情况就是这样。
也许克拉克还不知道呢。如果他是在摆弄电脑,那就一定是背对着窗户和这条路的。
不过贾米森太太很可能还会开车出去的。她从飞机场开车回家,也许并没有停下来去买食物——她应该径直回到家里,想好需要买些什么,然后再出去一趟。那时候克拉克可能会见到她。而且天黑之后,她家里的灯也会亮起来的。不过此刻是七月,天要很晚才会黑。她也许太累了,灯不开就早早儿上床了。
再说了,她还会打电话的。从现在起,什么时候都可能会打的。
这是个雨下得没完没了的夏天。早上醒来,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雨声,很响地打在活动房子屋顶上的声音。小路上泥泞很深,长长的草吸饱了水,头上的树叶也会浇下来一片小阵雨,即使此时天上并没有真的在下雨,阴云也仿佛正在飘散。卡拉每次出门,都要戴一顶高高的澳大利亚宽边旧毡帽,并且把她那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和衬衫一起掖在腰后。
来练习骑马的客人连一个都没有,虽然克拉克和卡拉没少走路,在他们能想起来的所有野营地、咖啡屋里都树起了广告牌,在旅行社的海报栏里也都贴上了广告。只有很少几个学生来上骑马课,那都是长期班的老学员,而不是来休假的成群结队的小学生,那一客车又一客车来夏令营的小家伙呀,去年一整个夏天两人的生计就是靠他们才得以维持的。即令是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现在也大都出外度假去了,或是因为天气太差而退班了。如果他们电话来得迟了些,克拉克还要跟他们把账算清楚,该收的钱一个都不能少。有几个学员嘀嘀咕咕表示不满,以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从寄养在他们这儿的三匹马身上,他们还能得些收益。这三匹马,连同他们自己的那四匹,此刻正放养在外面的田野里,在树底下四处啃草觅食。它们的神情似乎都懒得去管雨暂时歇住了,这种情况在下午是会出现片刻的,也就是刚能勾起你的希望罢了——云变得白了一些,薄了一些,透过来一些散漫的亮光,它们却永远也不会凝聚成真正的阳光,而且一般总是在晚饭之前就收敛了。
卡拉已经清完了马厩里的粪便。她做得不慌不忙的——她喜欢干日常杂活时的那种节奏,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现在她又走到环形训练跑道那里去看看地上够不够干,说不定五点钟一班的学员还会来呢。
通常,一般的阵雨都不会下得特别大,或是随着带来什么风,可是上星期突然出现异象,树顶上刮过一阵大风,接着一阵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大雨几乎从横斜里扫过来。一刻钟以内,暴风雨就过去了。可是路上落满了树枝,高压电线断了,环形跑道顶上有一大片塑料屋顶给扯松脱落了。跑道的一头积起了一片像湖那么大的水潭,克拉克只得天黑之后加班干活,以便挖出一条沟来把水排走。
屋顶至今未能修复,克拉克只能用绳子编起一张网,不让马匹走到泥潭里去,卡拉则用标志拦出一条缩短些的跑道。
就在此刻,克拉克在网上寻找有什么地方能买到做屋顶的材料。可有某个清仓处理尾货的铺子,开的价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或是有没有什么人要处理这一类的二手货。他再也不去镇上的那家海·罗伯特伯克利建材商店了,他已经把那店改称为海·鸡奸犯捞大利商店,因为他欠了他们不少钱,而且还跟他们打过一架。
克拉克不单单跟他欠了钱的人打架。他上一分钟跟你还显得挺友好的——那原本也是装出来的——下一分钟说翻脸就翻脸。有些地方他现在不愿进去了,他总是让卡拉去,就是因为他跟那儿的人吵过架。药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位老太太在他站的队前面加塞——其实她是去取她忘了要买的一样什么东西,回来时站回到他的前面而没有站到队尾去,他便嘀嘀咕咕抱怨起来了,那收银员对他说,“她有肺气肿呢。”克拉克就接茬说,“是吗,我还一身都有毛病呢。”后来经理也让他给叫出来了,他硬要经理承认对自己不公平。还有,公路边上的一家咖啡店没给他打广告上承诺的早餐折扣,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克拉克便跟他们吵了起来,还把外带的一杯咖啡摔到地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店里的人说,就会泼到推车里一个小娃娃的身上了。他则说那孩子离自己足足有半英里远呢,而且他没拿住杯子是因为没给他杯套。店里说他自己没说要杯套。他说这种事本来就是不需要特地关照的。
“你脾气也太火爆了。”卡拉说。
“脾气不火爆还算得上是男子汉吗?”
她还没提他跟乔依塔克吵架的事呢。乔依塔克是镇上的女图书馆员,把自己的马寄养在他们这里。那是一匹脾气很躁的栗色小母马,名叫丽姬——乔依塔克爱逗乐的时候就管它叫丽姬博登。昨天她来骑过马了,当时正碰到她脾气不顺,便抱怨说棚顶怎么还没修好,还说丽姬看上去状态不佳,是不是着凉了呀。
其实丽姬并没有什么问题。克拉克倒是——对他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想要息事宁人的。可是接下来发火的反而是乔依塔克,她指责说这块地方简直就是片垃圾场,出了这么多钱丽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克拉克说:“那就悉听尊便吧。”乔依倒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当即就把丽姬领回去,卡拉本来料想会这样。可是原来总把这匹小母马当作自己小宠物的克拉克却坚决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牵扯了。自然,丽姬在感情上也受到了伤害。在练习的时候总是跟你闹别扭,你要清理它的蹄子时它便乱踢乱蹬。马蹄是每天都必须清的,否则里面会长霉菌。卡拉得提防着被它瞅冷子咬上一口。
不过让卡拉最不开心的一件事还得说是弗洛拉的丢失了,那是只小小的白山羊,老是在畜棚和田野里跟几匹马做伴。有两天都没见到它的踪影了。卡拉担心它会不会是被野狗、土狼叼走了,没准还是撞上熊了呢。
昨天晚上还有前天晚上她都梦见弗洛拉了。在第一个梦里,弗洛拉径直走到床前,嘴里叼着一只红苹果,而在第二个梦里——也就是在昨天晚上——它看到卡拉过来,就跑了开去。它一条腿似乎受了伤,但它还是跑开去了。它引导卡拉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的跟前,也就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去它——也就是弗洛拉——从那底下钻过去了,受伤的脚以及整个身子,就像一条白鳗鱼似的扭着身子钻了过去,然后就不见了。
那些马匹看到卡拉穿过去上了环形马道,便全都簇拥着来到栏杆边上——显得又湿又脏,尽管它们身上披有新西兰毛毯——好让她走回来的时候能注意到它们。她轻轻地跟它们说话,对于手里没带吃的表示抱歉。她抚摩它们的脖颈,蹭蹭它们的鼻子,还问它们可知道弗洛拉有什么消息。
格雷斯和朱尼珀喷了喷气,又伸过鼻子来顶她,好像它们认出了这个名字并想为她分忧似的,可是这时丽姬从它们之间插了进来,把格雷斯的脑袋从卡拉的手边顶了开去。它还进而把她的手轻轻咬了一下,卡拉只得又花了些时间来指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