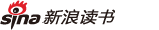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作家名片】
刘勇,男,笔名“格非”,生于1964年,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老舍文学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有关文学的问答
格非
冯唐:很多作家都面临过一个问题,创作停滞了一段就很难再写,或者写的水准和以前有一定距离。你十年没写,怎么恢复的状态?
格非: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冯唐:对写作技艺提高的追求,会成为继续写作的动力么?
格非:会。说句老实话,我在看博拉尼奥(智利作家)的《2666》之前,还是有一点狂妄的。但是我看一章,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发现,自己跟他差距还是蛮大的。这让我有点吃惊。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就会热血沸腾,会被煽动起写作的欲望。
冯唐:你在大学里教写作,你觉得写作是可以教的吗?
格非:小说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冯唐:可以定义一下,你心目中好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格非:要丰富,方法上最好能够简洁,在基本生存上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超越到哪去呢?可能是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比如说接近上帝。另外像日本的小泉八云,他的作品读完了之后,能让我们心里产生某种向善的要求。或者,有助于去了解我们欲望的秘密。欲望在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它还在控制我们,我希望好的作品能够带我来穿透这些。
冯唐:你、余华等人都曾被人称为是先锋小说家,在结构、写作上都作出了很多尝试,为什么近年这些尝试反而少了?
格非:那是年轻时的状态。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冯唐:这是做了结构性探索之后的回归吗?
格非:不能说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跟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刚开始写作,刚好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形成了巨大影响。一开始接触的都是现代主义作品,当然就对抽象的、观念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但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重新看其他类的作品,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变化那就是白痴。这可能跟人的年龄,经验的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肯定和时代有关系。今天的80后、90后他们刚开始接触的作品就和我们不一样,有的是从日本的、韩国的开始的,比如村上春树这种类型的。也许他们最终能走出这个影响,也许走不出来。当年我们要走不出来,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家,在当年做过一些探索,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如此而已。
冯唐:你跟同辈的作家聚的时间多吗,频率高吗?还谈文学吗?
格非:很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这些哥们原来在80年代的时候见一面,除了文学什么都不谈。现在是相反,见了面什么都可以谈,唯独不谈文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造成的,当然你要谈,别人也可以跟你谈,但是大家都不谈,彼此都心怀鬼胎一样,大家都不触及这个话题。
冯唐:现在你教书、做研究、阅读和创作,关系怎么摆法?
格非:对我来说,阅读是生活里最愉快的事情。阅读并不是一种求知,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然你在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书,其实我事后想想,背后是有种逻辑的。比如说你苦闷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快乐的书,肯定会去找也许能帮助你的书。我有段时间很苦闷,有一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就是保罗?蒂里希的《生存的勇气》。研究跟教学这方面这是本职工作,也就是必须做的。
冯唐:你怎么看个人声望?当年马原很羡慕你,说你30岁就已经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了,而且在《收获》上。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格非:我记得,我没觉得那有什么。我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当然我对写小说还是野心比较大,但对于出名什么的没有太大野心。名声这个东西,它会给人造成错觉,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人类有时想想很悲哀,人会对一种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着迷,然后你会受制于它。艾略特曾经讲过一句话—荣誉和安宁不能共处一室。这个话我们很早就知道。
【作品选介】
难懂的快感
语 谌
《褐色鸟群》注定是一篇你读过就难以忘却的小说,当然不止因为它不好懂。这部小说曾号称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但却很好看。
从最外在的方面说,《褐色鸟群》带给我的首先是语言上的快感。“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格非的语言从容而诗意,浸泡着丰富的回忆,勾起人的怀旧情绪。我的周围仿佛弥散升腾起茶色的烟雾,氤氲着歌谣湖畔的水汽。而当这样的语言与这篇小说里扑朔迷离的叙事相遇时,语言就显得格外神秘,扣人心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这里的语言是诡异的,当故事还没有展开,当“我”还没有与“棋”相遇之时,语言已经为后面的叙事营造了绝好的氛围。对于一个看似没有逻辑的混乱的故事而言,也许,只有这样诗意而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才能拽着读者,陪文中的“我”走到故事的末尾。
而当我们进入到故事本身时,我们发现,世界在被格非一点点颠覆着。小说发表于1988年,而“我”讲述的1992年到“歌谣湖畔”再遇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回忆”,属于未来的时间。小说开头所写的“我”与“棋”的第一次相遇则是比1992年还要靠后的未来。小说的结尾写道:“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这样时间漫延到了更加不可知的地方。我们的时间被颠覆了,回忆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交错在“我”与“棋”混乱的叙述里,混成一潭。而当故事展开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是前后两层的,不同的叙述视角在重复中交织着,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共同编织成一个故事。令人费解的是,所有我们前面已知的事实,到后面都会被颠覆,最终构成一串类似埃舍尔怪圈的系列圆圈。这一点评家们都有论及,郭宝亮将之比喻为俄罗斯套娃式结构。圆圈概括起来有三重: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往事;小说的最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二个圆圈,许多年前“我”从城里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之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她说她从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第三个圆圈,“我”在追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与女人和“我”讲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间构成相似与矛盾。这三个圆圈之间存在相互否定(矛盾)与肯定(相似)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而故事的细微之处,前后矛盾就更多。比如“我”自称自己蛰居在“水边”,而棋则说“我”是住在“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我”跟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到断桥,看到她从桥上过去,而桥边“提马灯的老头”则否认女人从这桥上经过;更诡异的是,后来这个女人称当时在桥边的是她的丈夫;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粪池里,而“我”却看见棺材里男人的尸体似乎动了一下,而且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倘若我们可以《罗生门》中不同人的讲述归因于在一个罪案中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那么《褐色鸟群》中不同的叙述则显得荒诞得突兀——我们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动机,到小说的最后,都分不清黑白真假。
这样的叙事是完全符合先锋小说的特质的——在叙事的迷宫中自由穿行,去找寻人物内心的奥秘和意识的流动。而格非的这篇小说尤甚。季红真先生认为《褐色鸟群》“由于过于抽象而丧失了叙事的本性,成为一种形式的哲学。”格非的确是在放纵着自己的文字,任它们在存在与虚无的混乱中冲击读者的意识,来完成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格非并没有忘记叙事的本性,只是《褐色鸟群》中的叙事,遵循了格非设定的哲学逻辑。格非明显受到了萨特等一拨人的影响。按照存在主义,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属于“自为存在”的性质,但这些都不属于与人无关的“自在存在”。《褐色鸟群》的叙事,就是在“自为存在”向“自在存在”的转换中,完成对存在与虚无的终极叩问。陈晓明论述得相当精辟:“格非把关于形而上的时间、实在、幻想、现实、永恒、重现等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叙述结构结合在一起。‘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随着叙事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在回忆与历史之间,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我认为,格非想要描绘的,是他眼中的存在与虚无混杂着的荒诞世间,而他将这世界的荒诞,浓缩在了一个关于“性、梦幻与感觉”这些人类最神秘领域的故事里。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质疑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都在痛恨着这个世界的荒谬,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当我们在格非的故事中完全迷失了支配着的所谓“逻辑”月“定式”,迷失了时间与空间时,我们获得的也许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感悟,这就是阅读快感的由来吧,虽变态,但真实。
上一篇:曹禺戏剧思想的美学内涵
下一篇:叶圣陶先生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