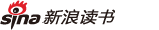编者按:近日,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3期,这是该杂志第一季度推出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期卷首语中说:“我们一直在热切盼望着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时代人物气质的现实题材力作的不断涌现……本期发表的长篇小说《经山海》,或可给这一期许中的大路留下较为明显的足迹。”这是一部有历史厚重感的小说,新时代的历程与个人的历程,都处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他在创作谈中说:这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向齐鲁文化和山东大学的致敬之作,承载着齐鲁大地上传承已久的人文精神,在新时代里建功立业。

吴小蒿刚走出办公楼,就见郭默骑着摩托车从大院最后面的文化站过来了。因为车子太旧,声音特别大,车后冒的青烟也清晰可见。
郭默将车停住,漂亮的小脸上现出笑容:“吴镇长,你家里有车,也不开到楷坡,还要我用这破摩托驮你。”吴小蒿将一条腿迈上她的车后座,说:“我把车开来,孩子上学怎么接送?我必须留给孩子她爸。”“再买一辆。”“那怎么可能?我还当着房奴,每月要还房贷呢。”郭默说:“能当城里的房奴,也是一种幸福。我们住着镇里不花钱的房子,可是把孩子耽误了,乡镇小学,教学质量太差,这都什么年代了,老师上课竟然还用本地土话,愁死我了!咱们先看楷碑,你坐好,咱走。”
来到楷坡村后,只见地势越来越高,最后发展成一座小山冈,上面长了一些松树。走了没有多远,郭默向路边一指:在那里。吴小蒿下车,见路边有一块花生地,地头上立着一块青石碑。
郭默讲,听老人说,当年这里的老楷树又粗又高,树荫能遮住半亩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楷坡成立供销合作社,有人提议杀这楷树,解木板做柜台面。一帮人来杀,用锯锯了几下,伤口竟然流血,他们吓得跑掉了。供销社主任不信邪,说哪里是血,只是树汁子而已,他亲自拉锯,拉了整整一天,才把这树杀倒。解了一页页又宽又厚的板子,放在用砖垒起的柜台上面。她小的时候,供销社还没垮,她去买东西,曾经摸着三尺多宽的柜台面板,想象楷树有多么粗。
吴小蒿早在《隅城地名志》上读到,楷坡之所以叫楷坡,是因为过去此处长满楷树。她问郭默,现在楷坡还有没有楷树。郭默说,没有。林业站在全镇普查过,一棵也没有。因为这树珍贵,早就叫人杀没了。最后一棵老楷树让人杀了之后,只剩下这块碑。
吴小蒿痛心疾首,近前去看那碑。碑在中间断成两截,又用水泥接在了一起。幸好碑文还算完整,是一首五律:
不晓何人植
悠悠矗古今
孔林瞻圣树
尘海化人心
屡感风霜重
常观天地阴
书生楷下坐
睹叶泪沾襟
---道光二十三年暮秋隅城教谕
申瑶步施闰章《子贡手植楷》原韵
她看看诗后落款,忽然想起,读大三那年春天,全班集体坐火车去曲阜参观孔庙、孔府、孔林,在孔子墓前见过“子贡手植楷”,但那是一段枯木。讲解员说,楷树是圣树,树干挺拔,枝繁叶茂,为众树榜样。当时她凝视那段楷木,肃然起敬。她还记得,楷亭后面还有一通碑,上有赞诗,但诗的内容现在已经忘了。她用手机百度一下,才知道那里刻着清初诗人施闰章的《子贡手植楷》:
不辨何年植
残碑留至今
共看独树影
犹见古人心
阅历风霜尽
苍茫天地阴
经过筑室处
千载一沾襟
郭默说:“这诗是什么意思?我读不懂。”
吴小蒿说这是清代隅城县教育局长申瑶写的,沿用了施闰章的诗韵。他去曲阜瞻仰过子贡手植楷,想以孔子学说教化人心,但觉得困难重重,十分失望,到这棵大楷树下坐着,看着落叶暗暗落泪。
郭默说:“这人感情还挺丰富。”
这么一句评语,让吴小蒿哭笑不得。
郭默向山冈一指:“今天时间挺紧,咱们就不去挂心橛了。”
“挂心橛?”
郭默说,过去渔民出海打鱼,在望不见村庄的时候,就用陆地上的一些突出物做地标。楷坡沿海渔民打鱼回来,一见到这座小山从海面上冒出来,就知道快到家了,安下心了,所以就把这山叫挂心橛,意思是自己的心挂在上面。吴小蒿看看那座山冈,心想,这个名字起得好。
下一个目标是丹墟遗址。二人离开楷坡走七八公里,几百米宽的蓼河出现在眼前,大片蓼花把两岸染成紫红色。往东边河口瞭一眼,能看得见黑色的泥滩和蓝色的海面。过大桥,往西拐,到一个村头,郭默将车子停在一块花岗岩石碑前面。吴小蒿下了车,只见碑上正中刻有“丹墟遗址”四个大字。她早就知道这处是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迹,但没来看过。她在市博物馆里见到,从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几件薄如蛋壳的黑陶杯工艺高超,代表了中国史前制陶业的最高水平。
吴小蒿问,丹墟遗址的文化层在哪里?郭默向周边指点着说,丹墟村下面,周围,都有文化遗存,总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在她们面前,有一道刚刚开挖的水沟,从断面看,耕作层之下真有厚厚的文化层,黑乎乎的泥土里,陶片星星点点。还有一些红色土块,一看就是烧过的。吴小蒿明白,这是四千年前的一个窑址。这儿之所以叫丹墟村,遗迹之所以叫丹墟遗址,就是因为这些废弃的古窑。
吴小蒿读中国古代史,对史前时代特别感兴趣。她经常遐想:人猿揖别之后,人类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走入文明的?然而,书上告诉人们的,除了神话就是传说。幸亏那些考古学者从荒野中、地表下,将史前人类的遗留物一点点寻出,让它们说话。在中国,他们发掘了一系列文化遗址,于是就有了河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这些文化类型中,吴小蒿最尊崇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在济南东边几十公里,她大学期间曾去那儿实习。据学者推断,龙山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当时中华大地上万邦林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凭借德行与才能,威仪天下,四海咸服。就在这个时期,华夏民族开始生成,东方文明拉开了大幕。
她打量着眼前的田野,庄稼一季一季,人类一茬一茬,四五千年恍然而逝。与那时相比,人类有了哪些进步?又有了哪些退步?
看罢丹墟遗址,再去看霸王鞭。二人骑车东去,到钱湾渔港向南一瞥就看到了。那里,岸边礁石向海中延伸,节节相连,渐渐变细,像一条长鞭。吴小蒿编《隅城文史》时看过资料,得知这霸王鞭退潮时露出来,亮鞭于海天之间;涨潮时隐入水中,只显一道幽幽的鞭影。当地人传说,这是楚霸王当年遗落在这里的一支鞭子。
吴小蒿走近霸王鞭,被它的气势深深震撼:波涛汹涌,它安之若素;鸥鸟起落,它无动于衷。郭默说,霸王鞭是一块凶险之地,当地人没有敢上的。外地人不知好歹,看到这里景象别致,兴致勃勃上去拍照或者捡牡蛎,一不小心就会落水,落水后很难爬上来,每年这里都有人死掉。
吴小蒿看见,那道礁石到了岸边,还是呈凸起状,延伸出二百多米,竟然到了很大的一座庭院门口。门上方挂了一块匾,上面写着“神佑集团”四个大字。她见过一些集团公司总部,但没有一个是在这种大院里。她问郭默,神佑集团老板是谁?郭默用冷眼向那边一瞅,压低声音说:“虎鲨!”吴小蒿不明白,郭默告诉她,虎鲨是鲨鱼中最凶猛的一种,神佑集团老总慕平川,也像虎鲨一样凶狠,当地人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离开霸王鞭,郭默带吴小蒿向西面的山区奔去,她已经和石屋村郑书记说好了,看了那里的“香山遗美”,在村里吃饭。
刚走到半路,吴小蒿的手机响了。她让郭默把车停下,掏出手机接听,原来是刘大楼的。刘大楼说,书记午后两点半要找她谈话,让她准时到书记办公室。她想,书记找我谈什么呢?心里像塞了一把乱草。
走了一会儿平路,再驶上一条山道,吴小蒿感觉到海拔高度不断提升。车子停在山腰,郭默说,这就是香山,海拔一百八十六米,摩崖石刻就在上面。吴小蒿一转脸,看见了远处的大海和海中的鳃岛,就问这里离海有多远。郭默说,十二公里。这片山区,被称作楷坡镇的“青藏高原”。
有敲锣打鼓的声音从村中传出。郭默皱眉道:“这是怎么鼓捣的?难听死了!”吴小蒿听见,那些响器配合得不好,没有劲头,节奏也乱。
两人往高处走了几十米,就到了一处悬崖。悬崖高达二十多米,下面有凹进去的一个大洞。洞口上方,用颜体正楷刻着“香山遗美”四个大字,落款为“康熙十年隅城县令郑理题”,阴文沟槽里的红漆脱落殆尽,斑斑驳驳。
吴小蒿早就知道这里,因为她看过《隅城县志》记载:三户农人居于香山石屋,某日,有一骡至此,负囊皆白银,农人坚守之。忽有仓皇来寻者,言标识悉符,尽数归还。谢以金,坚辞弗受。县令郑理得知,题“香山遗美”以葆彰。
进去看看,见石屋外高内矮,石壁被烟熏得乌黑。中间有一堵石墙,墙上有门洞窗洞,里面隔出几间,有石桌石床。吴小蒿想到,石屋村的先人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仍保持着传统美德,真了不起。当年那头骡子,为何会驮着银子到这里来呢?她走到东面的高处打量一下,发现山下有一条南北大路,那是隅城去苏北的主要通道。很可能是骡子的主人中途休息,没把牲口拴牢,它就挣脱束缚跑到山上来了。
郭默说,咱们到村委吃饭去。二人沿着坡度很大的山路去了村里。此时,锣鼓声再度响起,却节奏分明,带了许多花样,十分好听。
来到村部大院,见里面一群老汉敲打响器,旁边站了几个年轻人。一位黑瘦老汉,穿一领蓑衣,抡两支鼓槌,是个核心角色。他打鼓时两眼放光,极其兴奋,蓑衣毛随之抖动,让自己成了一只老刺猬。
郭默带吴小蒿走进办公室,见几个中年男人正在抽烟。一个四十来岁的站起来,对郭默笑着说:“哎哟,大歌星来了,快坐!”郭默说:“歌星算什么,我把吴镇长带来了。人家是凭本事考上的副科级干部,周一才来咱镇报到。”她向吴小蒿介绍,那人就是这个村的书记郑立前。
吴小蒿问,外面敲锣打鼓干啥,郑立前向院子里瞅一眼:“这帮老汉,谝他们有能耐。”他告诉吴小蒿,今天下午村里有人结婚,要去接新娘,可是年轻人都不在家,敲锣鼓找不齐人。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半大小子,把村里公有的响器拿出来操练,敲出的声音乱七八糟。会弄响器的几个老汉过来说,俺敲给他们听听,就在这里敲起来了。打鼓的老汉是这帮人的头头儿,外号“老花鼓”,因为他能把鼓点敲出花儿来。
吴小蒿早就听说,过去隅城人在傍晚娶亲,但现在城里人已经改在了上午,没想到山里的风俗依旧。她看着那位“老花鼓”说:“他们敲得这么好,应该有名堂吧?”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半大老汉说:“他们敲的叫‘斤求两’。”郭默眼睛一亮:“这就是《斤求两》呀?我知道这个打击乐牌子,但是从没听过。”说罢,就拿出手机到门口录像。
腊月将至,吴小蒿把郭默叫到办公室商量,准备在春节前举办一场“楷坡春晚”,庆祝十八大召开,迎接蛇年到来。
她们商定,在“楷坡春晚”上力推石屋村的《斤求两》。不仅在镇里表演,还要到区里、市里表演,使之列入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此,她俩又专程去了一趟香山。这次,吴小蒿骑了自己的摩托车。她觉得,在乡下工作离开车子不行,就和由浩亮商量,买了一辆摩托车,骑到了楷坡。
来到石屋村,让村干部把那帮老人召集起来,一遍遍敲打。吴小蒿让郭默录下视频,然后请老人讲解为什么叫“斤求两”。“老花鼓”讲:过去称东西,一斤等于十六两,但是算起来很麻烦,要把两化成斤才行,古人就总结出了一套口诀: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四二五,五三一二五……有人用锣鼓家伙把这些算法敲出来,这就是“斤求两”。
郭默将双手捂上胸口,眼睛瞪圆:“什么?把算法敲出来?那是数学,这是音乐,怎么可能?”吴小蒿说:“你别忘了,简谱就是用数字记录的。”“这口诀我不懂,彻底蒙圈。什么是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吴小蒿说:“在十六两制里,一两等于零点零六二五斤,二两等于零点一二五斤,以下类推。”“鼓点怎么能把口诀敲出来呢?”吴小蒿说:“让老人们再敲给咱们听。”
老人又开始演奏,并且提醒她俩,重点听鼓点。吴小蒿在手机里搜出“斤求两”口诀,边看边听。她听见,在大锣、小锣、钹、铙热热闹闹的敲击中,鼓点果然有玄机。突然,它敲了六下,间隔几个小节再敲两下,再间隔几个小节敲五下。六、二、五,这是把“一两”敲出来了。往后,她全听懂了,就微笑着报出口诀:“一、二、五,二两!一、八、七、五,三两!……”直到把十五两全部报出。老人们非常兴奋,用更加欢快有力的打击表示“一斤”的到达。
吴小蒿听罢感叹:因为含有“斤求两”,这种鼓谱非常复杂,一般人真是演奏不了。
“老花鼓”敲下最后几个鼓点,指挥大家收住家伙,用鼓槌指着吴小蒿说:“你这个镇长厉害。三十年来,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听懂,你是第一个!”
郭默连连摇头:“我可听不懂,真的听不懂。吴镇长,我服你了!不过,这也怨不得我,老祖宗为什么要把一斤搞成十六两,多麻烦呀。”
吴小蒿读历史时看过资料,向她解释:先秦时期,古人运用杠杆原理发明了木杆秤,把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合计定为十三两一斤,所以秤上每一两的标记也叫“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加上人间的“福、禄、寿”三星。这样,天上人间,合计为十六星,把十六两定为一斤,并诏令天下,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少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就会减福折寿。
“老花鼓”说:“对,老辈人传下两句话: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
从石屋村回来,吴小蒿就坐到办公室,用电脑写申遗报告。她查阅资料,仔细研究,觉得《斤求两》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是在“香山遗美”的故事发生地发现的,证明这个山村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孔子说过,“礼失求诸野”,此言不虚。
她突然来了写作冲动,此后用两个晚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锣鼓铿锵〈斤求两〉》,署名“吴小蒿、郭默”。
赵德发:写一部有历史感的小说
——《经山海》创作谈
我多年前购得一本《历史上的今天》,读得入迷,因为我从中发现了历史的另一种面貌。我们在常规史书上读到的历史是线性的,这本书上的历史却是非线性的。常规史书是现实主义写法,这本书却有魔幻色彩。上下几千年,恍然成为一片森林,森林由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棵大树组成。大树参天而立,每一棵代表一天,上面挂满果实。果实有甜有酸,有苦有辣;或赏心悦目,或滴血瘆人。单独观看一棵树,忽而回到古代,忽而跳到现代;忽而去了外国,忽而回到中国,给我的冲击力格外强烈。
因此,当《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约我写一部反映新时代的小说时,我立即想到了这部书给我的感受,决定用“历史上的今天”结构小说,并写出一位历史感特强的主人公——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毕业的女镇长吴小蒿。
新时代,也是“历史上的今天”。战军主编说过这样的话:“新时代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带着新时代的印迹。”我深以为然。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巨变之后,对新时代的感受尤为强烈。2018年春天我去沂蒙山,在扶贫工作队长的陪同下,站在古生代寒武纪的海底沉积物、今天的“透明崮”上看下面的花海人烟,想到近年来我们国家的日异月殊,沧桑感溢满心间。
吴小蒿不是意念的产物。我出生于农村,从25岁起就在公社、县委工作,后来成为专业作家,还是一直关注农村,对乡镇干部较为熟悉。他们处于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工作繁重,十分辛苦。与社会中任何群体一样,这个群体也是形形色色,鱼龙混杂,荼毒百姓的败类屡见不鲜。但就大多数而言,他们能够认真履职,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看待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与前辈有所不同。尤其是,一些优秀者会用历史眼光观照当下,有强烈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既接地气,又明大势,成为乡村振兴的扛鼎人物。其中一些女干部,德才俱备,不让须眉。但这些女干部并不像当年“样板戏”里的江水英,也有凡人俗举,七情六欲。在家庭与事业上,她们很难两全,有诸多烦恼乃至种种磨难。我多次倾听过她们的讲述,为她们的经历慨叹不已。基层政治中的女性在新时代的表现,便成为我这本新作的主要内容。
于是,吴小蒿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她在农村出生,被重男轻女的父亲视为蒿草,考进大学后热爱史学志存高远,却被迫嫁给一位品质恶劣的“官二代”。她到海边一座城市工作,在机关坐班十年后深感厌倦,就参加干部招考,下乡当了副镇长。从此,开启了她个人的“新时代”,也让我们看到了黄海之滨一个半农半渔之镇的“新时代”。
这位体重不足百斤的小女人,可怜,可爱,可敬。她的经历与命运,让我牵肠挂肚。在长达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心思全在她的身上,甚至为她哭过几回。见我恍恍惚惚魂不守舍,老伴打趣,说我“精神出轨了”。
对吴小蒿的这份情感,还改变了我的写作手法。我有这样的经历:外孙女住我家时,我因为特别喜欢她,看她时常常舍不得转移目光。写这部书时面对吴小蒿,我也是“目不转睛”。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一直聚焦于她,“一镜到底”。有朋友说,没想到长篇小说能这样写。我说,笔随心走,墨与情谐,这是创作的金科玉律。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有点儿历史感。没有历史感的人,对当下的时代与生活,就不能有深刻的感受与思考。因此,我让吴小蒿习惯性运用历史目光,将自己面对的事情放在历史背景下思考,因而,她在楷坡镇的一些作为便具有了历史意义。她喜欢《历史上的今天》一书,在书中记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女儿点点也效仿母亲。于是作品的每一章前面,都有一组“历史上的今天”:书中记的、小蒿记的、点点记的,一条一条,斑驳陆离。读者会看到,新时代的历程与个人的历程,都处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耐人寻味。
这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向齐鲁文化和山东大学的致敬之作。我1988年考入山大中文系办的作家班,两年间深受山大学术风气和齐鲁文化传统熏染。那时在我心目中,山大的文史楼是一座圣殿,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系有“八马同槽”,文学系有“四大金刚”,都是在全国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们的徒子徒孙,有好多直接教过我,或以著作哺育过我。所以,我让作品主人公毕业于那里,承载着齐鲁大地上传承已久的人文精神,在新时代里建功立业。
2018年深秋,山东大学作家班举办入学三十年聚会,我写了一首七律,承蒙班主任老师、著名学者兼书法家王培元先生当场挥毫写出。其中有这么两句:“常闻夏雨催新果,莫怨秋风撼老枝”。这部作品,算是我在夏天里饱受雨露滋润,在秋天里结出的一个果子吧。
2019.1.16
上一篇:叶兆言:有了大运河这一捺,中国“人”字就站住了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