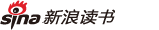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
2013-04-18 16:07:01 发布者:phpcms 来源:本站
宋海泉在他回忆白洋淀时期的文章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一群少男少女,一群在白洋淀插队的20多岁的青年,在远离亲人的异乡,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不便的水乡,他们偶然地聚在一起,黄昏,他们告别,各回各的村子,水乡的雾霭已弥漫了堤岸。“我们默默地走着,一片静谧,只有水中的月亮在跳跃,随着粼粼水波化作片片金光。忽然,身后传来了歌声,那是她在为我们送行,月色里已看不见她的身影。”①这情景一直感动着我。这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在华北水乡,在70年代初始的日子里,对于我们,那是孤独、寻求、忧伤与向往并存的青春时代。诗在我们心中自然地生长。是时代把我们投射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上,也许,这就是我们不幸中的有幸。
讨论白洋淀诗歌群落,我们必须回到60年代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特殊年代的一批青年,被迫放逐到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穷乡僻壤。希望的破灭,心灵的折磨,前途的渺茫,青春的向往,内心的抗争与生命的活力融为一体,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批优秀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成长的。
1968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1966年6月开始,所有大、中、小学都已停课三年之久,几百万大中学生如何处置已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1968年下半年,我们是在不断的送别中度过的。
我相信“文化大革命”会是人类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它将会被史学家们反复研究并引发人们不断的思考。当然,本文不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而是研究在这个宏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文学团体“白洋淀诗歌群落”。
白洋淀诗歌群落产生的社会背景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的一片洼地,古代称之为“祖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有人研究,战国时代荆轲刺秦王的告别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即在白洋淀之南,今安洲地界,燕太子丹率众送至易水之南,那里有“古秋风台碑”记载了这一历史典籍。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的唯一的水乡,距北京市150公里。太行山脉以东有九条河流曾注入其中,俗称九河下潲。白洋淀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由大小几十个淀组成,淀淀相连,四周有堤坝围拢,堤岸曲折,当地人称之为千里堤。淀中有几十个自然村落,大多以芦苇和捕鱼为生。出入都要依赖船只。它不同于中国的江南水乡,冬天结冰,秋春两季有封冻和解冻期,交通不便。30、40年代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
60年代末,白洋淀地区也同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行政管理为人民公社方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行政机构分为两个派别,一部分占据县城,一部分占据一个大的村镇。白洋淀因为人口多,没有接受知识青年到那儿插队的任务。当时,北京的大多数中学生被分配到陕西、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边远地方。到白洋淀插队的是一批借助毛泽东的指示“各地农村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而自由组合,自己联系的中学生。他们是一批思想活跃,有反抗精神的青年。
杨桦在他的《白洋淀的回忆》一文的“逃难者们”一节中写到:“被群众‘专政’八个月后,1969年初,我被获准每周末回家一次,并让我准备赶赴山西,同本学校的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他在一个周末遇到了朋友周舵,周的处境与他相似。“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革命的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也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重大。听到消息几天后,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1969年三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三趟,办了近二十个人的插队手续……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80%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②
正如杨桦所讲的,当时到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中,家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由于生活经历的原因,他们不再盲目地相信那些虚假而空洞的政治说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他们是一批有一定社会文化见识的,思想敏锐的青年。
在白洋淀地区插队的中学生有几百人,其中有多半是天津回乡知青,北京学生大多数是自行组合,自己联系来白洋淀的,没有带队管理的干部。这样,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知青少了许多羁绊,再加上与北京相距较近,信息方便,它的特殊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孤岛上的小群体,它是一个同北京及全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开放的体系。
宋海泉在《白洋淀琐记》中有这样的论述:“应该说,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没有必然的血缘联系,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龛 ,借助这个小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根在北京。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了自己的果实。”③
在白洋淀插队的潘婧在《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里是这样描述那个年代的:“至今已有了关于北大荒、陕西和云南知青的纪实文学,似乎没有人认真写过白洋淀。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约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干部子弟,这一小小的群体却有别于上述地区的几百万人,他们不肯接受硬性的指令和安排,试图脱离原来的集体,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白洋淀。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有着如诗一般的凄清的湖水。最初是孙犁的散文使我们想到这片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地方。而后来,起始于70年代的‘朦胧诗’就发源于这片久远而浪漫的湖水。……似乎没有什么苦难能泯灭青年人浪漫的情怀。随后的一个冬天,我们却体验了一种原始得近于残酷的物质生活。有一段时间,精神和物质,理想与现实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④
总之,白洋淀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诗歌群落,有以下几点:1、有一批思想敏锐并具有独立思考的人。2、环境相对宽松,有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3、距北京较近,信息来源多,与外界交流方便。
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和与其相关的读书活动等,还将在下面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称谓与范畴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称谓是准确而明了的。1994年中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的活动,当年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和北京70年代文化沙龙的参与者以及诗人、诗评家二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寻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大家一致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命名是恰当的。老诗人牛汉先生指出:这个名词本身很有诗意,群落一词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与当时诗人们的处境与写作状态相符。
在此之前,一些书中将这一文学现象称为“白洋淀诗派”,这一称谓显然有一些勉强,因为,白洋淀的诗人们既不是一个诗歌团体,也不是一个流派。他们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的一批松散的诗歌写作者,他们有着一般流派的相似之处,但在诗歌主张与创作方式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他们还是一批自然的诗歌创作者。
还有一点也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它有着更为宽泛的涵盖与包容。它与当时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龙有着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
诗人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一文中写到:“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了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和沙龙主持人。她是人民大学附中老高一的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我们(注:指芒克、岳重、多多)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人性强悍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等。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⑤
在白洋淀插队的周舵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中也写到:“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边无界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缝隙……”⑥
白洋淀距离北京150公里,当时乘火车再换汽车,六至八小时可以到达。有的插队知青骑自行车12小时,可从白洋淀回到北京。因为交通的相对便利,许多人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也有很多从各地回到北京的知青,为躲避北京经常的户口检查而到白洋淀暂住的,白洋淀各村知青之间的来往也是频繁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与北京地下文学沙龙密切相关的文化氛围。
在黑龙江插队的诗人马佳在一篇访谈录中说:“我进入诗歌界,最主要的引路人就是郭路生。他的成就、他的人生和他的不幸是一体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真诚地面对自己。这是我所认识的诗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当然,正是因为过于真诚,他才会疯。我呢,当时是介乎于郭路生和白洋淀群体的一个中间点,我是在夹缝之中……在白洋淀那会儿(实际上大多在白洋淀插队的都呆在北京),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养病……只有这些不是喜欢在外头的人,才能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小的团体。而白洋淀离北京最近,所以,这该叫什么群落呢?……我作为一只候鸟呢,无非是穿行在南北之间……只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这样一群人。”⑦
从这些叙述里我们不难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发生是和北京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密不可分的。自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的文化青年中,已经开始了一种相悖于当时所谓正统文化的潜流,从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到郭路生文革初期的诗歌写作,从兴起于70年代初的北京地下文化沙龙到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文化的潜流为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朦胧诗浪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也不难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除了以当时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为主体外,还有与白洋淀密不可分的一些诗人,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一群体的有机部分。
白洋淀当时有许多与诗歌写作有关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有的研究哲学,社会学,有的研究经济学,有的喜欢绘画,有的研究音乐,总之,那是一批并没有被生活的残酷现实压垮的有志青年,他们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加之来自其他各个地方的知青和来自北京的一些对文化有追求的青年,这些无疑都为白洋淀的诗人们注入了思想的活力。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有这样几部分诗歌写作者最终合流而成的:一些“文革”前就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兴趣以及后来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开始写作的青年;一些“文革”前受当时流行的朗诵诗的影响开始写作的青年;一些受西方及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开始写作的青年。这三部分人在1972年前后,在当时那种特殊的近于文化荒漠的大环境中,在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启发下,开始合流为追求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一个诗歌写作群体。他们也是后来在80年代初兴起的“朦胧诗”的源头。
白洋淀知青中当时写诗的大约有二、三十人,后来与现代主义诗歌追求相关的人并不在多数,还有一些虽没有在白洋淀插队,但与白洋淀诗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江河,1969至1973年期间他曾先后在白洋淀居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首诗是在我插队所在的村子里写出来的。
宋海泉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我们村的地理位置在进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我们常常接待很多同学。一两天的停留不论,住上一两个月的,亦有人在,像甘铁生、陈淮子等。而在寨南住得时间最长的,应该说是于友泽(江河)了……友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文学性的背景。他全文抄录了白郎宁的《十四行诗集》,全文抄录了热梅尔拉依梯斯的组诗《人》,甚至还临摹了书中的木刻插图。还带来了内部出版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寨南期间,友泽尚未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首诗大概是1971年在北河庄(林莽插队的村子)写成的……”⑧
此外还有孙康(方含),他在距白洋淀30公里的徐水县青庙营村插队,与白洋淀的诗人们过从甚密。北岛、郭路生、袁家方、史保嘉等诗人,还有甘恢理、陈凯歌、甘铁生也都到过白洋淀。
我以为,白洋淀诗歌群落既有地域的限定,又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涵盖,它是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以白洋淀这片华北水乡为依托,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有生长潜力的诗歌群体。
白洋淀诗歌群落与当年的地下读书活动
根据宋永毅《文革中的黄皮书和灰皮书》一文记载:“……文革以前出版,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的著作约有1041种……这些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访谈,下列的‘内部读物’对文革一代人的思想曾发生过极大影响……”⑨宋先生列出了37种,其中我读过的有《人、岁月、生活》、《解冻》、《厌恶及其他》、《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带星星的火车票》、《多雪的冬天》、《落角》、《白轮船》等十种。我觉得除了他列出的一些社会和政治书籍外,还有有关社会思想的一些文选,还有存在主义的一些书籍也在一批青年中流传着。同时西方现代绘画和音乐也在这批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潘婧在回忆中说:“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杜申科和热梅尔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并不喜欢。”⑩
徐浩渊在她的《我的反思》中写到:“冬闲时,扒火车(没有钱,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的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了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11)
那个时期,白洋淀的诗人们也同样加入了这些带有自发性和启蒙性的读书与创作活动之中。
杨桦回忆说:“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等插队知青……他们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书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了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满满的全是书……我借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司汤达的《红与黑》,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12)
根据我的记忆,这种读书活动在插队之前已经开始了。文革开始,大中学生运动很快就不再是主流。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最初的红卫兵许多也因父母受到批判而成为“狗崽子”,不得不退出政治的舞台。从那时起,有一些青年便开始躲到书本中。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读了一百多本古今中外的小说和诗歌,成为我后来创作生涯开始的前奏。
“文革”的遭遇,使一代人开始了觉醒。他们开始真正地了解了自己和世界,他们的写作真的进入了生命与内心,他们开始找到了文学艺术的根本。那个时期的读书活动像一种催化剂,使一代人的心灵发出了光芒。
与白洋淀诗歌群落相关的诗人们
除了更早一些的“太阳纵队”和郭士英那一代诗人与白洋淀诗歌群落有比较模糊的关联外,后来,在诗歌上有较多影响的几位诗人几乎都与白洋淀的诗人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连接。他们是郭路生(食指)、马佳、北岛和江河。
根据杨桦回忆,郭路生(食指)在1969年秋天曾到白洋淀的李庄子。当时,何其芳女儿何京颉在那儿插队。他除了和知青们来往外,还拜访了当地的农民诗人李永鸿。他曾想从山西转到白洋淀插队,但没有实现。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郭路生作为那个时代的开拓者对白洋淀诗人们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1969年,江河到白洋淀,在我插队的村子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带来了《相信未来》、《烟》、《酒》等几首郭路生的短诗。那年,我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小诗。郭路生的诗深深地触动了我。后来,我又在宋海泉那儿抄了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和《鱼群三部曲》(发表时改为《鱼儿三部曲》)。这些诗时常伴随着我们,在白洋淀的日子里,有很多个夜晚大家一起朗诵着或一个人在默默地诵读。郭路生是走在那个时代最前边的诗人,他启发了一代新人的成长。
马佳在黑龙江插队,后因病在北京疗养,他曾和多多、芒克、根子、彭刚等十多个人组成过一个小沙龙。他的诗歌我在白洋淀曾经读过,还在抄诗本上摘录过他的诗句。如:“我像秋天的野果/那样沉重/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除了酒/还是酒/二十岁以前/天天都是节日”。马佳虽不在白洋淀插队,但和白洋淀的诗人有着相同的诗歌渊源。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受郭路生的影响较大:“真正对我影响深的是郭路生。郭路生是跟我姐关系非常好,他们年龄一样。我一直是仰视郭路生。所以我们一开始交谈的时候,受到这些诗人、外国诗以及这些黄皮书的影响,而这些诗人和这些黄皮书都是郭路生向我介绍的。”(13)可以说马佳是在郭路生和白洋淀诗人之间的一名诗人,他和白洋淀诗歌群落有着特别的联系。
江河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一直关系很好。尤其是文革后期我们的交往很多。他几次到白洋淀大多在我那儿住上一阵。前文提到,他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我插队的地方写出来的。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父母在文革中受难,但他还是被分到了一个北京的小街道工厂里工作。他读书很多,在北京当时的青年诗人群体里是大家公认的。他早期和在白洋淀写的诗歌都没有拿出来发表,他那时的作品具有很好的抒情性,在那时的诗歌圈子里有较多的流传。后来他发表的作品都是1978年后创作的,和以往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江河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他们以外,其他艺术门类的人与事,无疑是与诗人们的创作相关的,这里不再详细论述。有些早期和晚期与白洋淀有关的诗人,如马佳、多多和其他人文章里都曾提到过的:依群、史保嘉、袁家方、北岛、彭刚、鲁燕生、鲁双琴、张廖廖等,当然还有后来和白洋淀有许多联系的严力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主要代表性诗人
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人与事已经变得模糊而疏远,当时在白洋淀,在那片凄清的湖水上,到底有多少知青动笔写过诗,已无法明确统计。但相对于其他门类的作品,诗歌依旧是幸运的。因为诗歌的非直接性,情感性,易于流传性而使许多当年的作品保存了下来。虽然,当年的诗人们都曾因为失望、沮丧或担心政治的迫害而损坏、丢失过一些作品。仅是这些得以保留下的作品,已经可以让我们确认,他们是一批对当代诗歌有贡献的诗人。
宋海泉是白洋淀最年长的知青。他是1966年北京清华附中高三的学生,学养很好。为人善良,绰号“老羊”。文革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他现在保留了两首长诗《海盗船谣》和《流浪汉之歌》。前一首是他当年抄送给去白洋淀游历的赵振先,二十多年后,赵将这份原稿通过我交还了宋海泉。另一首保留在我的抄诗本上。老羊的作品有古典风格,思想深沉,悲凉的情感流淌于咏唱之中。他的家中也曾一度有许多知青回城后聚在一起,交流社会认知和艺术思考等。当时,经常往来的有郑义、甘铁生、江河、崔健强、刘满强、顾益等。我的诗歌和当时没有完成的一篇小说,就曾在他的家中朗读过。老羊联系面很广,他们的村子是到县城的必经之路,许多外省的知青来到白洋淀都曾在他们那儿停留。
方含,原名孙康,是北京三十五中的学生。前文写到,他在距白洋淀30公里的徐水县青庙营村插队。无论在白洋淀还是在北京,他与白洋淀的诗人都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家里也曾有过聚会的小团体,70年代初,我在他家的聚会中认识了翻译家江枫先生。孙康文革中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后来他的有洛尔迦诗风的创作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有一年的春节,孙康到我家玩,我让他看了我新完成的两首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和《悼1974年》。他读后一再嘱咐我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以免引来麻烦。后来,他想编一本那几年朋友们创作的诗歌选集,要走了我的一些诗,由于当时根本不具备条件,诗集一直没有出来。那些年,虽然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大家依旧在为诗歌努力着。
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三剑客”芒克、根子、多多,他们三个是北京三中初二七班的同班同学,乘同一辆马车到白洋淀,又同样都写一手好诗,故被称为“三剑客”。他们对当时的诗歌写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认识最早的是多多。我们在北京的家相距很近,但第一次见面是在白洋淀宋海泉他们那儿。记得还有陶雒诵、赵京兴。那次赵刚刚从北京的看守所放出来,关于他们的情况,宋海泉的《白洋淀琐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那天我们彻夜长谈,从西方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从监狱生活到诗歌的写作。那时,多多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寻求。我还记得他早期诗歌中那些诗句。如:“我蹲在厕所里/公社的喇叭像饭碗”、“清晨/太阳升起来/照亮了真理那红赤赤的烂屁股”。经过了多年的寻求,多多可以说在诗歌的形式与方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我在一篇题为《穿透岁月的光芒》的文章中提到:“根子的作品不多,到目前仅存三首长诗和一些零散篇章。他曾被北京当时的地下诗坛誉为‘诗歌霸主’。他的一首《三月与末日》让当时的诗人们不无赞叹。记得70年代初的那些春天,我也被那样一种诗情所弥漫着,当我读了根子的这首诗,一切都释然了。我的一部分有关春天的诗稿就成了废品。说心里话,就我当时的写作实力,是无法达到他那种水准的。后来,根子以男中音考取了中央乐团。现在国外工作。也许是生活的变迁,也许是某种厌倦,他不再写诗。尽管有许多朋友活跃在80年代的诗坛上,但他一向不参加诗歌的活动。但他的诗并没有被人们忘记。”(14)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他的《白洋淀》一诗,我将他的作品与内容大体相近的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进行了比较,这两首诗同样是对希望破灭者的情感描述。食指和根子年龄相差四岁,诗歌的写作时间也相差了四年,但食指诗中的希求与向往在根子的诗中已不复存在。食指是浪漫主义倾向的,而根子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写作方式的尝试。就中国近代诗歌史而言,1973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那一年,一批新艺术的追求者开始汇集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根子是走在前面的人。
我和芒克在白洋淀时期无缘相见,是70年代末在《今天》的聚会上才相识的。但他的诗我很早就读到了。我在白洋淀时期的抄诗本上有他的许多摘句。近些年我们交往较多。芒克从白洋淀时期的创作,到80年代末的《没有时间的时间》,我认为,他用自己的诗歌,为我们这一代人勾画出了一幅心灵的图谱。他的诗还有待于批评家们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芒克是一位天才的类似叶赛宁一样的诗人,他的诗中充满了灵性。
白洋淀诗歌群落还应提到杨桦和赵哲。
杨桦原名宁润平。文革中因思想活跃而被批斗,在学校强制劳动八个多月。为了躲避迫害,更名改姓,到白洋淀插队。他的父亲是部队的干部,有一些流传的黄皮书,就出自他的家中。他的诗有一种高贵之气。与诗歌相比,他更偏爱哲学,他的诗歌创作不多,留下来的就更少了。
赵哲是家里的独生女,为了不给已经在文革中挨整的父母和爷爷找麻烦,和同学一起到白洋淀插队。她的写作基本是属于自然主义方式的。
还有一些诗人我没有论述到,如与芒克同村的白青,赵庄子的周陲等,因为他们的诗歌所知不多,故不便杜撰。关与我自己,在文章中已多处提到,这里也不再赘述。
白洋淀诗歌群落价值的总体认识
一、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以北京为根柢、以白洋淀为基点的一批诗歌写作者的集合。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70年代初始阶段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二、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诗歌流派,是一批有一定现代主义文化追求的青年写作者。他们还处于自由写作状态,是一批松散的、有多方面相互连接的文化青年。
三、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写作者,由于文革和插队生活的体验,他们开始摒弃了传统教育中那种表面化的、虚假的写作,在怀疑和反思中注重了自己的生命的真挚体验。
四、由于读书活动和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启发和影响,他们开始打破了被封闭了多年的门户。衔接了五四以来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自觉地追求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
五、就当代文学史而言,从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到郭路生,在这条追求诗歌现代主义的道路上,白洋淀诗歌群落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这一领域,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汇合。
六、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朦胧诗”的源头,这批诗人经过了十年的努力,为80年代“朦胧诗”席卷全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诗歌艺术探索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我还想就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研究提出我的一点希望。白洋淀诗歌群落仅仅是那些年中国文革文化中的一点,它的发掘与研究具有典型的价值,也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读本,就此部分的陈述和研究还有待加强。本文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注释:
①、③、⑧宋海泉《白洋淀琐记》,《诗探索》1994年第4期。
②、(12)杨桦《白洋淀的回忆》,未发表。
④、⑩潘婧《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中国作家》1994年第6期。
⑤多多《被埋藏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9年第1期。
⑥周舵《当年最好是朋友》,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⑦、(13)《马佳访谈录》,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⑨宋永毅《文革中的黄皮书和灰皮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年8月号。
(11)徐浩渊《我的反思》,《世界日报》1997年3月30日。
(14)林莽《穿透岁月的光芒》,发表于《新创作》2000年第4期
讨论白洋淀诗歌群落,我们必须回到60年代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特殊年代的一批青年,被迫放逐到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穷乡僻壤。希望的破灭,心灵的折磨,前途的渺茫,青春的向往,内心的抗争与生命的活力融为一体,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批优秀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成长的。
1968年下半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1966年6月开始,所有大、中、小学都已停课三年之久,几百万大中学生如何处置已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
1968年下半年,我们是在不断的送别中度过的。
我相信“文化大革命”会是人类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它将会被史学家们反复研究并引发人们不断的思考。当然,本文不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而是研究在这个宏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文学团体“白洋淀诗歌群落”。
白洋淀诗歌群落产生的社会背景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的一片洼地,古代称之为“祖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有人研究,战国时代荆轲刺秦王的告别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即在白洋淀之南,今安洲地界,燕太子丹率众送至易水之南,那里有“古秋风台碑”记载了这一历史典籍。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的唯一的水乡,距北京市150公里。太行山脉以东有九条河流曾注入其中,俗称九河下潲。白洋淀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由大小几十个淀组成,淀淀相连,四周有堤坝围拢,堤岸曲折,当地人称之为千里堤。淀中有几十个自然村落,大多以芦苇和捕鱼为生。出入都要依赖船只。它不同于中国的江南水乡,冬天结冰,秋春两季有封冻和解冻期,交通不便。30、40年代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
60年代末,白洋淀地区也同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行政管理为人民公社方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行政机构分为两个派别,一部分占据县城,一部分占据一个大的村镇。白洋淀因为人口多,没有接受知识青年到那儿插队的任务。当时,北京的大多数中学生被分配到陕西、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边远地方。到白洋淀插队的是一批借助毛泽东的指示“各地农村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而自由组合,自己联系的中学生。他们是一批思想活跃,有反抗精神的青年。
杨桦在他的《白洋淀的回忆》一文的“逃难者们”一节中写到:“被群众‘专政’八个月后,1969年初,我被获准每周末回家一次,并让我准备赶赴山西,同本学校的学生一同插队,‘继续接受群众专政’……”他在一个周末遇到了朋友周舵,周的处境与他相似。“他劝我一同去白洋淀插队,一来可以躲开与学校革命的积极分子共同插队,二来鱼米之乡生活也不会太苦,又有离北京近便之利。对我来说,去白洋淀插队是从群众专政中逃命,干系重大。听到消息几天后,乘着学校大部分人将去插队的纷乱,我就去了白洋淀。”……“1969年三月,我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跑了三趟,办了近二十个人的插队手续……屈指一算,我所熟悉的同去落户的学生中,80%以上是‘文革’中落难家庭的子女。”②
正如杨桦所讲的,当时到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中,家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由于生活经历的原因,他们不再盲目地相信那些虚假而空洞的政治说教,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他们是一批有一定社会文化见识的,思想敏锐的青年。
在白洋淀地区插队的中学生有几百人,其中有多半是天津回乡知青,北京学生大多数是自行组合,自己联系来白洋淀的,没有带队管理的干部。这样,白洋淀的北京知青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知青少了许多羁绊,再加上与北京相距较近,信息方便,它的特殊自然环境也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插队知青。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孤岛上的小群体,它是一个同北京及全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开放的体系。
宋海泉在《白洋淀琐记》中有这样的论述:“应该说,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产生,同它本身的文化传统没有必然的血缘联系,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这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龛 ,借助这个小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根在北京。白洋淀诗歌群落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种都市文化。远而言之,它继承了五四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创建新诗学的努力。所不同的是它减少了以往不可避免的工具主义的倾向,多了一些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的终极关怀。近而言之,它对‘十年浩劫’曲折而坚韧的抗争。借助于白洋淀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结出了自己的果实。”③
在白洋淀插队的潘婧在《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里是这样描述那个年代的:“至今已有了关于北大荒、陕西和云南知青的纪实文学,似乎没有人认真写过白洋淀。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约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干部子弟,这一小小的群体却有别于上述地区的几百万人,他们不肯接受硬性的指令和安排,试图脱离原来的集体,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白洋淀。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有着如诗一般的凄清的湖水。最初是孙犁的散文使我们想到这片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地方。而后来,起始于70年代的‘朦胧诗’就发源于这片久远而浪漫的湖水。……似乎没有什么苦难能泯灭青年人浪漫的情怀。随后的一个冬天,我们却体验了一种原始得近于残酷的物质生活。有一段时间,精神和物质,理想与现实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④
总之,白洋淀之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诗歌群落,有以下几点:1、有一批思想敏锐并具有独立思考的人。2、环境相对宽松,有一个较为自由的空间。3、距北京较近,信息来源多,与外界交流方便。
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创作和与其相关的读书活动等,还将在下面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称谓与范畴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称谓是准确而明了的。1994年中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的活动,当年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和北京70年代文化沙龙的参与者以及诗人、诗评家二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寻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大家一致认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命名是恰当的。老诗人牛汉先生指出:这个名词本身很有诗意,群落一词给人一种苍茫、荒蛮、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感觉,与当时诗人们的处境与写作状态相符。
在此之前,一些书中将这一文学现象称为“白洋淀诗派”,这一称谓显然有一些勉强,因为,白洋淀的诗人们既不是一个诗歌团体,也不是一个流派。他们只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的一批松散的诗歌写作者,他们有着一般流派的相似之处,但在诗歌主张与创作方式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他们还是一批自然的诗歌创作者。
还有一点也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它有着更为宽泛的涵盖与包容。它与当时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龙有着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
诗人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一文中写到:“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了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和沙龙主持人。她是人民大学附中老高一的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我们(注:指芒克、岳重、多多)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人性强悍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等。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⑤
在白洋淀插队的周舵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中也写到:“70年代初,正是‘文革’混不讲理的黑暗时代,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位、身处异乡、非工非农的边缘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可能在群众专政无边无界的大网中觅得少许缝隙……”⑥
白洋淀距离北京150公里,当时乘火车再换汽车,六至八小时可以到达。有的插队知青骑自行车12小时,可从白洋淀回到北京。因为交通的相对便利,许多人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也有很多从各地回到北京的知青,为躲避北京经常的户口检查而到白洋淀暂住的,白洋淀各村知青之间的来往也是频繁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与北京地下文学沙龙密切相关的文化氛围。
在黑龙江插队的诗人马佳在一篇访谈录中说:“我进入诗歌界,最主要的引路人就是郭路生。他的成就、他的人生和他的不幸是一体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真诚地面对自己。这是我所认识的诗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当然,正是因为过于真诚,他才会疯。我呢,当时是介乎于郭路生和白洋淀群体的一个中间点,我是在夹缝之中……在白洋淀那会儿(实际上大多在白洋淀插队的都呆在北京),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圈子,是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养病……只有这些不是喜欢在外头的人,才能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小的团体。而白洋淀离北京最近,所以,这该叫什么群落呢?……我作为一只候鸟呢,无非是穿行在南北之间……只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这样一群人。”⑦
从这些叙述里我们不难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发生是和北京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密不可分的。自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的文化青年中,已经开始了一种相悖于当时所谓正统文化的潜流,从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到郭路生文革初期的诗歌写作,从兴起于70年代初的北京地下文化沙龙到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一文化的潜流为十年后席卷全国的朦胧诗浪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也不难发现,白洋淀诗歌群落除了以当时在白洋淀插队的诗人为主体外,还有与白洋淀密不可分的一些诗人,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一群体的有机部分。
白洋淀当时有许多与诗歌写作有关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有的研究哲学,社会学,有的研究经济学,有的喜欢绘画,有的研究音乐,总之,那是一批并没有被生活的残酷现实压垮的有志青年,他们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加之来自其他各个地方的知青和来自北京的一些对文化有追求的青年,这些无疑都为白洋淀的诗人们注入了思想的活力。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有这样几部分诗歌写作者最终合流而成的:一些“文革”前就对中国古典诗词有兴趣以及后来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开始写作的青年;一些“文革”前受当时流行的朗诵诗的影响开始写作的青年;一些受西方及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开始写作的青年。这三部分人在1972年前后,在当时那种特殊的近于文化荒漠的大环境中,在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启发下,开始合流为追求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一个诗歌写作群体。他们也是后来在80年代初兴起的“朦胧诗”的源头。
白洋淀知青中当时写诗的大约有二、三十人,后来与现代主义诗歌追求相关的人并不在多数,还有一些虽没有在白洋淀插队,但与白洋淀诗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江河,1969至1973年期间他曾先后在白洋淀居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首诗是在我插队所在的村子里写出来的。
宋海泉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我们村的地理位置在进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我们常常接待很多同学。一两天的停留不论,住上一两个月的,亦有人在,像甘铁生、陈淮子等。而在寨南住得时间最长的,应该说是于友泽(江河)了……友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文学性的背景。他全文抄录了白郎宁的《十四行诗集》,全文抄录了热梅尔拉依梯斯的组诗《人》,甚至还临摹了书中的木刻插图。还带来了内部出版的《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选》。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寨南期间,友泽尚未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首诗大概是1971年在北河庄(林莽插队的村子)写成的……”⑧
此外还有孙康(方含),他在距白洋淀30公里的徐水县青庙营村插队,与白洋淀的诗人们过从甚密。北岛、郭路生、袁家方、史保嘉等诗人,还有甘恢理、陈凯歌、甘铁生也都到过白洋淀。
我以为,白洋淀诗歌群落既有地域的限定,又应该有一个开放的涵盖,它是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以白洋淀这片华北水乡为依托,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有生长潜力的诗歌群体。
白洋淀诗歌群落与当年的地下读书活动
根据宋永毅《文革中的黄皮书和灰皮书》一文记载:“……文革以前出版,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的著作约有1041种……这些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访谈,下列的‘内部读物’对文革一代人的思想曾发生过极大影响……”⑨宋先生列出了37种,其中我读过的有《人、岁月、生活》、《解冻》、《厌恶及其他》、《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带星星的火车票》、《多雪的冬天》、《落角》、《白轮船》等十种。我觉得除了他列出的一些社会和政治书籍外,还有有关社会思想的一些文选,还有存在主义的一些书籍也在一批青年中流传着。同时西方现代绘画和音乐也在这批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潘婧在回忆中说:“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杜申科和热梅尔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并不喜欢。”⑩
徐浩渊在她的《我的反思》中写到:“冬闲时,扒火车(没有钱,偷坐车)回北京,看望别的地方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朋友。讨论会,辩论会,‘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大寨是不是唯一的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现实阶级应该怎么划分?’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无奇不有,海阔天空……这些知识青年的地下讨论会和被现代人称为‘地下沙龙’的自发性文学、艺术的学习和创作,犹如一线曙光,穿透了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宗教式崇拜。”(11)
那个时期,白洋淀的诗人们也同样加入了这些带有自发性和启蒙性的读书与创作活动之中。
杨桦回忆说:“一次到寨南村,认识了崔建强、宋海泉等插队知青……他们的书让我叹服。四个人把书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图书馆。用厚木板条钉成了一个大箱子,长一米多。宽也近一米,满满的全是书……我借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司汤达的《红与黑》,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12)
根据我的记忆,这种读书活动在插队之前已经开始了。文革开始,大中学生运动很快就不再是主流。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最初的红卫兵许多也因父母受到批判而成为“狗崽子”,不得不退出政治的舞台。从那时起,有一些青年便开始躲到书本中。我就是在那个时期读了一百多本古今中外的小说和诗歌,成为我后来创作生涯开始的前奏。
“文革”的遭遇,使一代人开始了觉醒。他们开始真正地了解了自己和世界,他们的写作真的进入了生命与内心,他们开始找到了文学艺术的根本。那个时期的读书活动像一种催化剂,使一代人的心灵发出了光芒。
与白洋淀诗歌群落相关的诗人们
除了更早一些的“太阳纵队”和郭士英那一代诗人与白洋淀诗歌群落有比较模糊的关联外,后来,在诗歌上有较多影响的几位诗人几乎都与白洋淀的诗人们有着密不可分的连接。他们是郭路生(食指)、马佳、北岛和江河。
根据杨桦回忆,郭路生(食指)在1969年秋天曾到白洋淀的李庄子。当时,何其芳女儿何京颉在那儿插队。他除了和知青们来往外,还拜访了当地的农民诗人李永鸿。他曾想从山西转到白洋淀插队,但没有实现。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郭路生作为那个时代的开拓者对白洋淀诗人们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1969年,江河到白洋淀,在我插队的村子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带来了《相信未来》、《烟》、《酒》等几首郭路生的短诗。那年,我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小诗。郭路生的诗深深地触动了我。后来,我又在宋海泉那儿抄了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和《鱼群三部曲》(发表时改为《鱼儿三部曲》)。这些诗时常伴随着我们,在白洋淀的日子里,有很多个夜晚大家一起朗诵着或一个人在默默地诵读。郭路生是走在那个时代最前边的诗人,他启发了一代新人的成长。
马佳在黑龙江插队,后因病在北京疗养,他曾和多多、芒克、根子、彭刚等十多个人组成过一个小沙龙。他的诗歌我在白洋淀曾经读过,还在抄诗本上摘录过他的诗句。如:“我像秋天的野果/那样沉重/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除了酒/还是酒/二十岁以前/天天都是节日”。马佳虽不在白洋淀插队,但和白洋淀的诗人有着相同的诗歌渊源。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受郭路生的影响较大:“真正对我影响深的是郭路生。郭路生是跟我姐关系非常好,他们年龄一样。我一直是仰视郭路生。所以我们一开始交谈的时候,受到这些诗人、外国诗以及这些黄皮书的影响,而这些诗人和这些黄皮书都是郭路生向我介绍的。”(13)可以说马佳是在郭路生和白洋淀诗人之间的一名诗人,他和白洋淀诗歌群落有着特别的联系。
江河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一直关系很好。尤其是文革后期我们的交往很多。他几次到白洋淀大多在我那儿住上一阵。前文提到,他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我插队的地方写出来的。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父母在文革中受难,但他还是被分到了一个北京的小街道工厂里工作。他读书很多,在北京当时的青年诗人群体里是大家公认的。他早期和在白洋淀写的诗歌都没有拿出来发表,他那时的作品具有很好的抒情性,在那时的诗歌圈子里有较多的流传。后来他发表的作品都是1978年后创作的,和以往的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江河与白洋淀诗歌群落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他们以外,其他艺术门类的人与事,无疑是与诗人们的创作相关的,这里不再详细论述。有些早期和晚期与白洋淀有关的诗人,如马佳、多多和其他人文章里都曾提到过的:依群、史保嘉、袁家方、北岛、彭刚、鲁燕生、鲁双琴、张廖廖等,当然还有后来和白洋淀有许多联系的严力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白洋淀诗歌群落的主要代表性诗人
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人与事已经变得模糊而疏远,当时在白洋淀,在那片凄清的湖水上,到底有多少知青动笔写过诗,已无法明确统计。但相对于其他门类的作品,诗歌依旧是幸运的。因为诗歌的非直接性,情感性,易于流传性而使许多当年的作品保存了下来。虽然,当年的诗人们都曾因为失望、沮丧或担心政治的迫害而损坏、丢失过一些作品。仅是这些得以保留下的作品,已经可以让我们确认,他们是一批对当代诗歌有贡献的诗人。
宋海泉是白洋淀最年长的知青。他是1966年北京清华附中高三的学生,学养很好。为人善良,绰号“老羊”。文革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他现在保留了两首长诗《海盗船谣》和《流浪汉之歌》。前一首是他当年抄送给去白洋淀游历的赵振先,二十多年后,赵将这份原稿通过我交还了宋海泉。另一首保留在我的抄诗本上。老羊的作品有古典风格,思想深沉,悲凉的情感流淌于咏唱之中。他的家中也曾一度有许多知青回城后聚在一起,交流社会认知和艺术思考等。当时,经常往来的有郑义、甘铁生、江河、崔健强、刘满强、顾益等。我的诗歌和当时没有完成的一篇小说,就曾在他的家中朗读过。老羊联系面很广,他们的村子是到县城的必经之路,许多外省的知青来到白洋淀都曾在他们那儿停留。
方含,原名孙康,是北京三十五中的学生。前文写到,他在距白洋淀30公里的徐水县青庙营村插队。无论在白洋淀还是在北京,他与白洋淀的诗人都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家里也曾有过聚会的小团体,70年代初,我在他家的聚会中认识了翻译家江枫先生。孙康文革中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后来他的有洛尔迦诗风的创作得到了大家的好评。有一年的春节,孙康到我家玩,我让他看了我新完成的两首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年岁》和《悼1974年》。他读后一再嘱咐我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以免引来麻烦。后来,他想编一本那几年朋友们创作的诗歌选集,要走了我的一些诗,由于当时根本不具备条件,诗集一直没有出来。那些年,虽然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大家依旧在为诗歌努力着。
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三剑客”芒克、根子、多多,他们三个是北京三中初二七班的同班同学,乘同一辆马车到白洋淀,又同样都写一手好诗,故被称为“三剑客”。他们对当时的诗歌写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认识最早的是多多。我们在北京的家相距很近,但第一次见面是在白洋淀宋海泉他们那儿。记得还有陶雒诵、赵京兴。那次赵刚刚从北京的看守所放出来,关于他们的情况,宋海泉的《白洋淀琐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那天我们彻夜长谈,从西方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从监狱生活到诗歌的写作。那时,多多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寻求。我还记得他早期诗歌中那些诗句。如:“我蹲在厕所里/公社的喇叭像饭碗”、“清晨/太阳升起来/照亮了真理那红赤赤的烂屁股”。经过了多年的寻求,多多可以说在诗歌的形式与方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我在一篇题为《穿透岁月的光芒》的文章中提到:“根子的作品不多,到目前仅存三首长诗和一些零散篇章。他曾被北京当时的地下诗坛誉为‘诗歌霸主’。他的一首《三月与末日》让当时的诗人们不无赞叹。记得70年代初的那些春天,我也被那样一种诗情所弥漫着,当我读了根子的这首诗,一切都释然了。我的一部分有关春天的诗稿就成了废品。说心里话,就我当时的写作实力,是无法达到他那种水准的。后来,根子以男中音考取了中央乐团。现在国外工作。也许是生活的变迁,也许是某种厌倦,他不再写诗。尽管有许多朋友活跃在80年代的诗坛上,但他一向不参加诗歌的活动。但他的诗并没有被人们忘记。”(14)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他的《白洋淀》一诗,我将他的作品与内容大体相近的郭路生的《海洋三部曲》进行了比较,这两首诗同样是对希望破灭者的情感描述。食指和根子年龄相差四岁,诗歌的写作时间也相差了四年,但食指诗中的希求与向往在根子的诗中已不复存在。食指是浪漫主义倾向的,而根子已经开始了现代主义写作方式的尝试。就中国近代诗歌史而言,1973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那一年,一批新艺术的追求者开始汇集在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根子是走在前面的人。
我和芒克在白洋淀时期无缘相见,是70年代末在《今天》的聚会上才相识的。但他的诗我很早就读到了。我在白洋淀时期的抄诗本上有他的许多摘句。近些年我们交往较多。芒克从白洋淀时期的创作,到80年代末的《没有时间的时间》,我认为,他用自己的诗歌,为我们这一代人勾画出了一幅心灵的图谱。他的诗还有待于批评家们的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芒克是一位天才的类似叶赛宁一样的诗人,他的诗中充满了灵性。
白洋淀诗歌群落还应提到杨桦和赵哲。
杨桦原名宁润平。文革中因思想活跃而被批斗,在学校强制劳动八个多月。为了躲避迫害,更名改姓,到白洋淀插队。他的父亲是部队的干部,有一些流传的黄皮书,就出自他的家中。他的诗有一种高贵之气。与诗歌相比,他更偏爱哲学,他的诗歌创作不多,留下来的就更少了。
赵哲是家里的独生女,为了不给已经在文革中挨整的父母和爷爷找麻烦,和同学一起到白洋淀插队。她的写作基本是属于自然主义方式的。
还有一些诗人我没有论述到,如与芒克同村的白青,赵庄子的周陲等,因为他们的诗歌所知不多,故不便杜撰。关与我自己,在文章中已多处提到,这里也不再赘述。
白洋淀诗歌群落价值的总体认识
一、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以北京为根柢、以白洋淀为基点的一批诗歌写作者的集合。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70年代初始阶段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二、白洋淀诗歌群落不是一个诗歌流派,是一批有一定现代主义文化追求的青年写作者。他们还处于自由写作状态,是一批松散的、有多方面相互连接的文化青年。
三、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写作者,由于文革和插队生活的体验,他们开始摒弃了传统教育中那种表面化的、虚假的写作,在怀疑和反思中注重了自己的生命的真挚体验。
四、由于读书活动和一批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启发和影响,他们开始打破了被封闭了多年的门户。衔接了五四以来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自觉地追求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
五、就当代文学史而言,从张郎郎为首的“太阳纵队”到郭路生,在这条追求诗歌现代主义的道路上,白洋淀诗歌群落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这一领域,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汇合。
六、白洋淀诗歌群落是“朦胧诗”的源头,这批诗人经过了十年的努力,为80年代“朦胧诗”席卷全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诗歌艺术探索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我还想就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研究提出我的一点希望。白洋淀诗歌群落仅仅是那些年中国文革文化中的一点,它的发掘与研究具有典型的价值,也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读本,就此部分的陈述和研究还有待加强。本文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注释:
①、③、⑧宋海泉《白洋淀琐记》,《诗探索》1994年第4期。
②、(12)杨桦《白洋淀的回忆》,未发表。
④、⑩潘婧《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中国作家》1994年第6期。
⑤多多《被埋藏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9年第1期。
⑥周舵《当年最好是朋友》,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⑦、(13)《马佳访谈录》,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⑨宋永毅《文革中的黄皮书和灰皮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年8月号。
(11)徐浩渊《我的反思》,《世界日报》1997年3月30日。
(14)林莽《穿透岁月的光芒》,发表于《新创作》2000年第4期


本站视点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