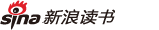灰喜鹊是一种极富感情的鸟儿,它们不仅知恩图报、勇救同伴、悼念亡者,而且还会记仇报复、团结抗敌。
知恩图报:被人类救养的灰喜鹊知恩图报,会与人们结下深厚的友情。2001年10月底,驻渤海某小岛战士站岗时,发现一只翅膀受伤的灰喜鹊,他将奄奄一息的灰喜鹊带回连队进行包扎治疗。半个月后,灰喜鹊在官兵的悉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官兵们将它带到山林里放生。不想它居然不忘救命之恩,带着两只小灰喜鹊在连队门前的一棵老槐树上安家落户,给连队增添了几分情趣。战士们经常撒些鸟食,让鹊妈妈带着小鹊来吃,很快灰喜鹊就和官兵成了好朋友。时间长了,这窝灰喜鹊把连队当成了自己的家。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们为“兵喜鹊”。
勇救同伴:一些鸟类有救助同类的护群特性,尤其是鸦科的灰喜鹊、乌鸦等大脑比较发达的鸟类更为明显。它们和人类一样具有很强的同情心,当同类受伤飞不动或受到侵害时,其他鸟儿会奋不顾身地飞过来营救。2001年6月,在北京天坛公园发生了“众灰喜鹊奋勇护同伴”的感人事情。一只灰喜鹊从高处掉下,摔在地上飞不起。数十只灰喜鹊飞过来,围着它盘旋飞翔,不停鸣叫,努力营救。
众鹊奔丧:灰喜鹊极富同情心,它们会像人类一样悼念死去的同类。1998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二处,一只灰喜鹊因年老力衰,不幸摔死在路边。600余只灰喜鹊从四面八方赶来“奔丧”。灰喜鹊们先是在老灰喜鹊的尸体旁盘旋飞翔,然后站在附近的树枝上齐声悲鸣,表示哀悼。隆重的“追悼会”从中午12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左右。无数游客驻足观看,为之感动。
复仇之神:灰喜鹊爱憎分明,对于伤害它们的人或动物不会屈服,反会报复。2001年6月一个早晨,在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一只大黄猫在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忽然,空中飞来二三十只灰喜鹊,直奔大黄猫,它们来势凶猛,就像一支复仇大军。大黄猫预感到苗头不对,飞奔起来,慌慌张张跑进一片茂密的草丛中,躲在里面,再也不敢出来。原来几天前它在树林中捉吃了一只灰喜鹊,当时引起近百只灰喜鹊的愤怒与哀鸣。它以为自己胜利了,却没想到灰喜鹊还有今日的反击和报复。
团结抗敌:当灰喜鹊遭遇强敌时,它们能团结战斗,不畏强暴,勇敢拼搏。在结成“战队”的灰喜鹊面前,连凶猛的老鹰也无可奈何。2002年10月一天,在某市街头,一只老鹰被一群灰喜鹊追赶逃窜。众灰喜鹊拍打着翅膀将老鹰团团围住,用尖利的嘴巴从四面八方向老鹰发起攻击。老鹰慌忙振翅欲飞,可它刚一展开翅膀,灰喜鹊们便拼命地向它身上啄去。老鹰抵抗了几分钟后,终于招架不住,找了个空隙逃到树上。据推断,这只老鹰一定是侵犯了灰喜鹊,才惹祸上身,遭此大劫(亿佰文学网)。
——全篇引言
第一章 应怜
新华社西安6月13日电:6月10日下午,在西安市友谊路市卫生学校家属院门前,约有10多只灰喜鹊为保护1只落地被车撞死的小喜鹊,不停地扑向企图靠近的行人,其护子之情令围观群众不时发出感叹。
据《西安晚报》报道,10日下午2时30分,记者闻讯后赶到现场,看到一只死去的小喜鹊躺在地上,只要一有人靠近其尸体,树上就会有一只或几只大喜鹊喳喳叫着扑来,并用爪子向人抓去。随行的摄影记者去拍小喜鹊的尸体时,一只大喜鹊鸣叫着贴着记者的头皮飞了过去,吓得记者出了一身冷汗。
据路边的目击者说,2时10分左右,一只不会飞的小喜鹊从树上掉下来,被一辆红色奥拓出租车撞伤。当时小喜鹊并没有死,还在不停地哀鸣。此时有十余只成年喜鹊围了上来,停在附近的树枝上,看护着小喜鹊。小喜鹊挣扎了几分钟后不幸死去,此后只要有行人走到小喜鹊尸体旁边,树上的灰喜鹊就鸣叫着扑来,有几个人险些被抓伤。
灰喜鹊的举动引得附近群众纷纷站在旁边围观。许多人对此事称奇,感叹地说,没想到小小的鸟儿也这样有情。记者在现场采访观察了一个半小时,离开时看到,这些灰喜鹊仍聚集在树上不愿离去。(大连日报)。
—— 第一章引言
所有的故事都从那一声凄厉的叫声中延伸而来。
我一直没有喝酒的习惯,但是我一直抽烟。
我的烟龄可以追溯到少女时代。应该是十三岁那一年。
当岁月的风尘渐渐隐没在斑驳的光与影的深处,那些在当初鲜活而具体的印象已经香消玉陨的时候,记忆里就只剩下一条暗红色的河流,像周身的血管一样时时缠绕着虽然发生但已经消失的一切。
六月二十三日,是的,是六月二十三日,镇上逢大集的日子。我攥着上官清给我的五角钱在人群里逡巡。
上官清说让我走累了的时候买块年糕充饥。
卖年糕的小商贩汗流浃背地拿衣衫下摆扇着那张像年糕一样颜色的脸,脸上流淌的汗水让我感觉嘴巴里一阵阵发咸发涩。
我忍受着肠胃饥饿的呐喊,转身向另外的街上走去。
在另外一条相对清静一些的街上,卖油条的大屁股老女人腰里扎着一条满是油脂的围裙,热火朝天地往翻滚着浪花的油锅里扔着一条条象牙色的面团。那些刚才还精瘦的面团在油浪花里翻几个个儿后开始发福,最后就欢欢喜喜地鼓胀起来,颜色也变成红褐色。
我攥着被汗水濡湿的五角纸币,站在炸油条的那锅滚油前,大脑里有种东西像黑夜里盛开的鲜花,越来越妖冶,越来越明晰。唾液腺在那一刻无比的发达,以至于口水顺着嘴角慢慢流下来都没察觉。
那张面值五角的纸币紧紧地贴在我的手心里,像一个忠诚的朋友一样用它的心紧贴着我的手心。我不舍得把这张好朋友一样的纸币送到大屁股女人油腻的手里,可是要得到一根膨胀起来的油条的念头却是那么强烈。
我眼巴巴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看着他们从大屁股女人手中接过用稻草绳捆好的一扎扎油条。我多么想摸一摸那些还冒着热气的松软的东西啊,我的心被那种奇异的幻想挠得异常不安。
赶集的人群开始减少,太阳已经由南方转移到西边了。
大屁股女人开始收拾各种工具,她把炉子里的木柴抽出来,插进旁边的污水桶里,嗤地一股白烟冒出来,淹没了柳条筐中剩下的几根油条。
我意识到这是我要得到一根油条的最后的机会了,我突然间俯下身子,张开嘴巴叼起一根粗大的油条,背转身,异常沉着地离开了大屁股女人。
大约在我离开大屁股女人十几步远的时候,我听见背后传来惊讶的叫声:咦?明明是剩下了六根油条的,怎么只有五根了?
我的双臂撒欢一样大幅度地摆动着,心脏的跳动淹没了各种小贩的吆喝声,清晰地震动着我的耳膜。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怀揣着那根来之不易的油条。来到废弃了的打麦场上。
月亮渐渐地升上来,像柳树叶儿一样紧贴在深蓝色的空中。一垛垛麦草散发出清草一样淡淡的香气。没有风,但是并不觉得燥热。
我找到一块干净的大青石坐下来,从怀里掏出那根油条。它早已经没有了刚出炉时的暄软,变得坚硬无比。我把它竖在眼前,定定地注视着,并且抽了抽鼻子。
就在这时候,一只黑色的大鸟凄厉地叫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追逐着远处一只黑色的影子消失在天空的尽头。
我觉得身体里的血管被那凄厉的叫声割裂开来,一种异样的感觉瞬间袭击了我的全身,随着就是一股粘乎乎的液体顺着大腿涌了下来。
我低下头。
我看到了一条蜿蜒爬行的暗红色的河流。
暗红色的河流变得声势浩大,犹如千军万马呐喊着冲进我的脑海。
我哭了。
那天夜里我很晚才回到家中。我像一只猫儿一样潜入到父母的房间里,摸黑找到养父上官清的香烟,又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子。
当恒大牌香烟像心脏一样抖动着燃烧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我就那样与香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应怜是东方慧儿沿着海岸线散步的时候捡到的。
东方慧儿说,当时看见不远处的雪松下有一只鸟儿扑楞着翅膀及力想飞到树上去,但是它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它焦急地叫喊着,小脑袋转来转去,似乎是在寻求同伴们的救助。可是,暮色四合中,所有的鸟儿都归巢了,周围见不到另外的鸟儿。
东方慧儿走过去,发现那是一只漂亮的灰喜鹊,它的头颈部呈现出明亮的黑色,背部是银灰色的,长长的尾巴则是令人眩目的明蓝色。野鹊镇简直就是灰喜鹊的天下,所以东方慧儿对这种鸟儿并不陌生,可是,她还从没有见过哪一只灰喜鹊生得如此美丽,简直让人怦然心动。她蹲下身子,那小东西警觉地往前直跳——它看来是受了重伤,根本就不能飞了。
东方慧儿发现它那两只黑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让人感到心跳加快的东西,她说她的心一下子就为之颤抖了。她轻轻地伸手将它握在手里,爱怜地抚摸着它毛绒绒的小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小可怜儿,你是受伤了吗?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来,让我看看你伤在哪儿。”
东方慧儿说她说着就仔细地检查起来。后来她发现那只灰喜鹊的肛门翻出了体外,并且呈现一种令人不忍卒睹的鲜红色,周围的羽毛全部被深红色粘稠的液体给纠结成块了。
东方慧儿明白这只鸟儿是受了内伤。她叹了口气,用双手呵护着它回到家中,找出治疗拉肚子的土霉素、PPA,还有一些头孢类的消炎药,在母亲司徒嘉禾的帮助下撬开它的嘴巴喂下去,然后用一只塑料盒子给它做了一张舒适的小床,铺垫上柔软的消毒棉。
第二天早晨,东方慧儿刚睁开眼睛就发现,母亲司徒嘉禾已经在替她给那只可怜的小鸟儿打扫卫生了。
司徒嘉禾见女儿醒了,举起一团半干的消毒棉说:“好了好了,它肚子里的毒气已经全部排出来了,你看,都把消毒棉染红了!”
东方慧儿这才发现那只灰喜鹊居然能够站起来了,黑褐色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毛绒绒的小脑袋一点一点,似乎在说:“是呀是啊,我已经快好啦!”
东方慧儿走过去,抚摸着鸟儿光滑的羽毛感激地望着母亲。
司徒嘉禾微笑着说:“你是个善良的孩子,这只鹊儿若懂得你的一翻苦心,也会感激你的。”
“鸟儿怎么能懂得人的心思呢?生物老师说,鸟儿的脑容量很小很小,不及人的万分之一哩。我是看它可怜才把它拾回来,可不是希望它感激我才这么做!”
东方慧儿指着蜷缩成一团的小鹊,不屑地说。
司徒嘉禾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没心没肺的女儿说:“你知道吗?在云南的瑶山,几乎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有鸟笼,瑶山的男人个个会玩鸟,懂捕鸟,善驯鸟。不会玩鸟驯鸟的男人不算男子汉。瑶族男子不论是上山砍柴、下地干活还是去开会、赶场、走亲,随手都拎着鸟笼。上坡下坎,小心地高高拎起鸟笼,宁可自己跌倒,也要保护心爱的鸟儿。困难时期,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给鸟儿喂小米和炒鸡蛋等精料!”
“是吗?那些瑶族人真是傻瓜,自己跌到了竟然还有心思保护鸟儿?自己都要饿死了还想着给鸟而喂那么好的饲料?妈,你这是从哪儿倒腾来的异端邪说啊?我不信呢。”
东方慧儿睁大一双清澈的眼睛,不信任地望着司徒嘉禾。
“孩子,你甭管妈是从哪儿弄来的消息,事实上鸟类一直就是人类的好朋友,不信你就以后好好观察去。”
“奇怪了,瑶山人为什么同鸟儿会有如此不寻常的关系呢?”
东方慧儿仍然迷惑不解,拿一根小木棍拨拉着蜷缩在那里一直不动的小鸟说。
“据说啊,在远古时代,瑶族祖先忽遇洪灾,浩淼的大水将作物全部淹没,连谷种也没留下。眼看种族就要灭绝,危难时刻,是鸟儿冒着危险飞涉重洋,从遥远的彼岸衔来谷种,使瑶山度过劫难,得以世代繁衍。于是,瑶族人同鸟儿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于死后坟前的木柱顶上也要刻上鸟儿,以让死者在九泉之下依然有鸟儿为伴。”
司徒嘉禾像老师给小学生讲故事一样,娓娓动听地叙述着。
“这都是传说而已,哪儿能有那么神奇的鸟儿呢?要是鸟儿们像你说的那样有灵性,那不是成了头条新闻了嘛。”
东方慧儿不服气地看看那只闭目养神的灰喜鹊,有些啼笑皆非地说。
“慧儿,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啊,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妈妈一向都相信,凡是万物生灵,只要是有生命的,就一定有着自己的性灵,你万不可轻视那些看似弱小的小生命啊,否则的话,它们就会给你苦头吃的!”
司徒嘉禾深有感触般地叹息着说。
“你那都是迷信活动,我才不信呢,你倒是说说看,那些在你眼中有灵性的小生命怎么给强大的人类吃苦头?”
东方慧儿对妈妈的论调非常反感,像找茬儿打架一样高声喊道。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田野里那些小小的蚂蚱够弱小了吧?可是,就是那些弱小的小东西,一旦多起来,就会让千万里良田变成一片白地!”
“那叫蝗灾!书上说,蝗灾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原因是春季降水量大了,蝗虫孵化率高。另外,人类破坏自然环境,使大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失去平衡,也是发生蝗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都有科学定论的事情啊,跟你所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呢,妈妈。”
“得得得,慧儿,妈妈讲大道理是比不过你,可是妈相信,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随意践踏,否则就有可能遭到惩罚。你现在挽救了这只小灰喜鹊的生命,妈妈真替你高兴呢。”
司徒嘉禾见女儿又搬出大道理来压她,只好偃旗息鼓,高挂出“免战牌”。
“我不怕什么东西来惩罚我,也不是为了得到报答才救这只小灰喜鹊的,我就是觉得它可怜罢了。”
“好好好,慧儿,妈不跟你谈论这些了。这只鸟儿要恢复体力还得养息几天,你好好照顾它吧。”
那之后,东方慧儿就成了这只灰喜鹊的“监护人”,她给它取了个乖巧的名字:应怜。
从十三岁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快乐。
在别人的眼中,我似乎一直都是个很不快乐的女孩子,因为我是被养父在襁褓之中抱养回来的。从我懂事开始,街坊们的耳语就震天雷一样在我耳边回荡:瞧瞧上官玉玲那孩子吧,打小就没有亲爹娘,那么伶俐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啧啧啧啧,可怜啊!
可是懵懂无直的我却并不觉得自己可怜,真的,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相反的,十三岁以前我一直很快乐地活着,活得像野地里的草,没有形状没有目标,一味地快乐,一味地疯长。那种快乐跟我的肉体与生俱来。
后来街坊们见耳语已经无法让我的不快乐觉醒,干脆就明确将我的历史提到大街小巷里来,他们怀着悲凉的心情,很沉重地大声叫嚣着:上官玉玲那孩子怎么会有个大姑娘母亲呢?真是老天不公哩!这么聪明伶俐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是个野孩子呢?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就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我是谁?我是个野孩子吗?我怎么会是个野孩子呢?什么是野孩子?野鹊镇上的人们为什么会用不同的眼光看我?我跟东方慧儿或者野鹊镇上的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吗?这些个问题不停地纠缠着我,弄得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叹气,让我怎么都快乐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很好奇地试探着问养父上官清:“我是谁?我是个野孩子吗?我的母亲是个大姑娘?”
上官清铁青着脸没好气地说:“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就是我的女儿!你怎么会是野孩子呢?野孩子是没有父母的,而你,不是有我这个父亲和她那个母亲吗?谁的母亲不是大姑娘?你听那些下流种子嚼蛆!”
上官清说完却突然拉起我的小手,用圆珠笔飞快地画了一丛盛开的白菊花,然后将我的小手放在他的大手里揉搓了好一阵子,颓然打开一罐啤酒,猛地灌进喉咙里去了。
我说过我不喜欢喝酒。但是我喜欢看别人喝酒,尤其喜欢养父上官清喝酒的样子。
上官清喝酒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老是不自觉地冒出“豪情万长”、“壮志凌云”之类的词语。
事实上上官清只不过是个青瘦的高个子男人,鼻梁上还架着一副代表文弱的无色眼镜。那副眼镜的镜片特别厚、特别大,整个占了上官清脸部的三分之一,这让他那双好看的眼睛看上去像盛在玻璃筐子里似的,闪烁着很不真实的光亮。
这个世界上喜欢喝酒并且喝高的人,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一种是喝高了躺倒就睡,发生十级地震都不能将其从美梦中弄醒;另一种是喝高了之后精神极度亢奋,即使面对着一根木桩子都要滔滔不绝地演讲大半天;还有一种人喝高了之后满大街小巷地游走,不走到酒精散失完毕精神清醒,是找不到家门的。
东方慧儿曾经跟我说过,她的父亲东方亮就属于后一种人。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东方慧儿听完我煞有介事的分析之后,用崇拜者的眼神望着我说:“上官玉玲你真神了!真的,我爸爸每次喝高了就满大街小巷走,也不管黑天半夜,也不管天晌日头西,就那么走啊走啊,见了谁都不答腔,就跟个瞎子似的。”
我嗤地笑出了声说:“你爸爸的外号不就叫‘东方无亮’嘛,看不见光亮了还不就是瞎子?”
东方慧儿一点儿都不介意,依然崇拜地望着我,真诚地问我:“你爸爸属于哪种类型啊上官玉玲?他也是喝高了满大街游走吗?”
我乜斜了东方慧儿一眼,很不屑地哼了哼鼻子说:“我爸爸上官清怎么会跟你爸爸属于同一个类型呢?我爸爸哪个类型都不属于!我爸爸喝高了的时候就吹口琴!”
我说这话的时候,眼前就满满展开一副魅力无比的画面:朦胧的月色下,青砖铺就的小院子里竹影婆娑,花香摇曳。上官清迈着轻巧的步子从屋子里走出来,眯着眼睛望一会儿如洗的碧空,然后找一只小板凳坐下,伸出长长的手臂把我揽在怀里,将那把有着碧绿格子的口琴横在嘴唇间略微用力,一声清脆的鸟叫就在小院子里回荡开来……
直到现在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能够听上官清吹口琴,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了。
可是这种幸福最初并不属于我,它属于我的养母欧阳百惠。
我不记得那时候我有多大,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一觉醒来依然在耳边回响的美妙的口琴乐音。
我有时候被那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爬到窗台上去探视,就会发现上官清怀抱着欧阳百惠,欧阳百惠一只手绕在上官清的脖子上,另外一只手不知去向。
上官清轻轻地吹动口琴,声音悦耳悠扬。这就是我为什么 常常趴在窗台上睡着的缘故。
我记得我的养母欧阳百惠为此不止一次地叹息说:“玉玲这孩子真让人害怕,放着好好的床不睡,为什么屡次趴在窗台上睡着了呢?奇怪她居然掉不下来!她是属猫的吗?”
欧阳百惠每次这样说我都会在内心得意好一阵子。我怎么会掉下来呢?有上官清那美妙无比的口琴声吸引着,我就像睡在云端里一样感到通体舒展。
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然后参加工作,然后从欧阳百惠的家中搬出去,搬到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子里。我找了工匠把家里所有的窗台都加宽至八十公分,加宽过的窗台成了我写作的最佳场所。月色朦胧的晚上,我写作累了的时候,就点燃一支法国熏香,在袅袅的香气里回忆童年时候每一件有趣的事情,那种感觉让我无比激动又伤感透顶。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是那声凄厉的鸟叫割裂了我身体里的某一处,取走了我少女时代所有的快乐,让我整个青春期充满血泪,处在一种灰暗和热烈交替的情绪状态中。它打破了我宁静的内心世界,将现实和梦境都涂满胆汁质和多血质——胆汁质使我充满暴力倾向,老想打碎什么东西,让那种碎裂的声音将耳朵震聋;多血质让我激情四溢,见到什么都产生拥抱的欲望,直到那种欲望将心灵折磨的疲惫不堪才能够得到一个安静的睡眠。
所以我对鸟儿没有什么好感。
东方慧儿抱着她的灰喜鹊应怜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水池子里洗着那条被暗红色的血液污染了的月经带。我吃力地用双手揉搓着它粉红色的胶皮,就像在揉搓自己那颗无助的心灵。
这之前我不止一次地在镜子前观察自己的脸部和大腿,那些地方的皮肤整齐划一地呈现出苍白的透明度,毛细血管清晰可见。我仔细观察过欧阳百惠和东方慧儿那些可见的血管,还有其他一些同学的,他们的血管很饱满,就像一根根灌满了水的管子,如果你仔细倾听,甚至能够听得到血液循环时发出的沽沽流淌的声音。而我的血管却是扁平状态的,即使带上qieting器也绝听不到任何表示生气勃勃的声音。
于是我确信我的血液已经被那声凄厉的鸟叫吸干了,这样一想我的大腿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仿佛又看见那条暗红色的河流顺着大腿汹涌而出,一直流到脚后跟,然后悄悄地渗进脚下的土地。
鸟叫和暗红色的河流频繁地出现在我十三岁的梦境中,折腾得我心力交瘁面黄肌瘦。
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猫儿一样悄悄地爬起来,从枕头里取出白天从上官清那儿偷来的香烟,点燃。大口大口地吞咽。
我很明确地知道我是在“吃”烟,而不是“抽”。因为白天我得乖乖地做老师的好学生,抽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抗拒不了那种辛辣的诱惑,于是就将烟丝装在口袋里,课间的时候就掏出来一点儿,像吃点心一样在嘴巴里细细咀嚼,然后不为人知地咽下去。
烟雾。
血。
泪水。
迷惑。
奇怪的是我从来不曾被烟雾呛得咳嗽起来,似乎我与烟之间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默契和姻缘。而庆幸得是直到好多天之后,上官清才发现他烟盒里的烟在莫名其妙地减少——那时候我已经取欧阳百惠而代之,在月色朦胧的晚上可以蜷缩在上官清瘦骨嶙峋的怀里倾听那美妙的口琴声了。
东方慧儿推开门走进来的时候,我正一边揉搓着月经带上的污血一边泪流满面。
我用了差不多一袋红花牌洗衣粉也没能将那些污秽洗干净,我又试图用肥皂来搓洗,可是,我的双手已经被洗衣粉和肥皂烧出好几个水泡来了,那些污秽依然顽强地粘覆在有着绿色小碎花的布面上,像一只只怪兽一样露着狰狞的面容讥讽我,嘲笑我。我精疲力竭。我伤心欲绝。
欧阳百惠将那条月经带扔给我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隐瞒鄙视的神色。她几乎是愤怒地将那条长方形的、有着四条长长的带子的月经带扔到我的小床上,回头冲着在院子里修剪葡萄枝的上官清说:“十三岁就来了,真不像话!我来的时候都十七了!”
就像回应欧阳百惠的责骂一样,一股粘腻的血液随着她愤怒的声音从我体内喷涌而出,情急中忙乱地深呼吸,期望能够用气力将那些使我脸面丢尽的脏东西吸回体内,可是没有用。艰难地站起身来,木椅子上已经是一片刀光血影。
那天傍晚,我第一次偷偷取出了上官清包在白色纱布中的那把口琴——上官清和欧阳百惠一起回娘家了,走时说要住一宿的。我踩着小板凳爬上欧阳百惠娘家陪送的鲜红色木柜子,从最深处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纱布包。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浑身已经被汗水浇透,胳膊和双腿已经颤抖的不成样子,一颗心已经从胸腔蹦到了口中。
我像完成某种庄严的仪式一样唰牙漱口,盘腿在板凳上坐定,生怕玷污了什么似的将口琴横在双唇之间。我突然发现自己口干舌燥,根本就没有能力将那些绿色的小格子吹响了。
我呆呆地坐在板凳上,欲哭无泪。
我想欧阳百惠说的对,我的确是太不像话了,十三岁就来了,真是的!为什么不让我像她那样堂堂正正地十七岁再来呢?
我把口琴贴在脸颊上开始嚎啕,眼泪汹涌澎湃,嘴巴里却奇苦无比,生涩的像吃了不熟的山柿子。
我正哭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大门被打开了,上官清一身酒气地走了进来。我们俩像两只不期而遇的猛兽一样,同时惊恐地呆住了。
片刻之后,上官清一个箭步扑过来,蹲下身子仰望着我消瘦的脸庞。
我闻到了他嘴里散发出的清香的酒气。
“我就知道你会出事的!”
上官清将脑袋俯在我盘起的双腿上,喃喃地低着嗓子说道。
我木然地呆坐着,身体僵硬得像条水泥檩条。
“傻丫头,你真是个傻丫头!别听那个女……你妈的,十三岁——十三岁也是正常的!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营养能够跟得上人身体的成长速度,所以很多孩子的成熟期都提前了。不用难过,也不用担忧害怕,女孩子要成长为真正的女人,都要经过这个时期的我的傻孩子,你长大了你知道吗?你是在长大!你是在成熟啊我的傻丫头!你应该高兴才是!”
上官清突然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用他硬硬的胡茬在我脸上亲昵地磨蹭着。
在上官清反复的强调中,我似乎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成熟了。我慢慢高兴起来,含着泪水的眼睛里绽开了一朵美丽的雏菊花。我紧紧地依靠在上官清温暖宽厚的怀抱中,幸福地寻找着成熟的快乐。
那一夜欧阳百惠没有回来。
从那一夜开始,我代替了欧阳百惠,坐在了上官清结实的膝盖上。
“你要快乐起来我的傻丫头!长大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甭担心,有爸爸在呢,爸爸会一直看着你长成一个真正的女孩。往后要是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就来告诉爸爸,爸爸愿意做你生活上最亲近的老师,好吗?不要去理那个……你的妈妈吧!她是有些神经质的,她一直都是有些神经质的,别理她好不好?我知道你是太缺少关爱和玩伴,爸爸是捕鸟的能手,明天就去给你捉两只雀儿,让它们陪伴你好不好?”
上官清说着,突然脸色一变,惊讶地提高了声音:“玲儿你抽过烟?!”
东方慧儿后来哭泣着说,她原本并没有想到要抱着应怜到我家,更没想到我会用那种怪异的方式杀死应怜,她之所以抱着应怜到我家来,是因为应怜突然之间不吃不喝,食物放在嘴边却连正眼都不看,似乎是在以绝食来抗议什么。她的母亲司徒嘉禾说,我的父亲上官清熟知鸟儿们的任何习性,要她抱着应怜到我家来求救。
东方慧儿耸动着双肩说,她也没想到那只灰喜鹊会突然挣脱开她的怀抱,蓦地直冲着我扑过来,不等在我的肩头站稳就拿它尖利的角质喙直啄向我的左眼!
我本能地将手中正洗着的月经带向上一挥,长长的带子就结实地缠住了应怜的脖子,并且像被人拽着一样穿过那些毛绒绒的羽毛越勒越紧!我在毫无意识中猛地站了起来,而应怜仍然用它带倒钩的爪子死死地抓住我的肩头,利爪透过薄薄的衣服深入到我的皮肉之中,殷红的血珠透过衣服渗了出来。
我的脑海里电光石火般响起那只大鸟凄厉的叫声,心中已经认定这只叫做应怜的灰喜鹊就是掠过高空用声音将我体内血管割裂的那一只了。
我想我的上辈子也许是灰喜鹊的天敌,因此应怜一见到我就把我的快乐夺走,然后又企图来啄瞎我的眼睛。想到这些我不仅悲从中来,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那是什么东西?你要勒死它了!”
东方慧儿绝望的哭喊声响起来,像山谷回声一样在午后的小院上空回荡着。
我蓦地松开手,那条带绿花的粉红色月经带颓然垂挂在应怜的脖子上,显得即滑稽又怪异。
应怜的脑袋倔强地昂仰着,圆圆的黄褐色的眼珠充满仇恨地盯视着我,似乎有无数的钢针正从它的目光中分化而出,钉进我身体的每一处。
我听见身体内部崩地一声,又崩地一声,像是单指猛挑吉他琴弦发出的声音,干脆而果断,凄厉而冰冷。
东方慧儿将应怜从我肩头撕扯下来的时候,那只灰喜鹊已经僵硬了。然而那两只利爪却一直深深地嵌进我的肌肉里,以至于东方慧儿不得不连我的皮肉一起往下撕扯。
后来当欧阳百惠狂怒地责问我“到哪里野把肩膀上的衣服撕扯坏了”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地承受着养母的责骂。我知道即使告诉她真相她也未必会相信,她会更加狂怒地咒骂我,说我是在找理由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欧阳百惠最后发现,她用尽全力伸出去的铁拳碰到的是一团软绵绵的云彩时,她冷静了下来,嘿嘿地冷笑着说:“上官玉玲,你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气死我吗?嗯,你跟你那个……你很妖啊,怪不得十三岁就来了!你不就是想气死了我,代替我掌管这个家吗?那好,你就走着瞧吧!”
欧阳百惠是在上官清不在家的时候向我挑战的。这么多年来她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她知道上官清在家里的时候该说什么,上官清不在家里的时候又该说什么。
那些天上官清到外地出差了,欧阳百惠一下子放松了许多,完全成了真实的欧阳百惠了。她把我关在家里,一天只让我吃一顿饭,而且还是馊的。
我像一只乞讨的狗一样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想抽烟,但是上官清不在家,家里的香烟已经没有了。
半夜里我攥着上官清走时留给我的一点零花钱在野鹊镇黑暗的街面上溜哒着。
风从野鹊河方向刮过来,送过来一阵阵夹杂着土腥味儿的野鹊粪便难闻的气味。我知道在我周围不远处的地方,一群群的野鹊正排好了阵势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它们是来为应怜报仇的。
我能感觉得到应怜死得有多么不甘心,我即使睁着眼睛也能看见它那双充满仇恨的黄褐色的眼睛。我没有想到要勒死它,真的。那条月经带是自己缠绕在应怜的脖子上的,我没有用一丝一毫的力气,可是它却自行其是地越勒越紧,直到应怜那颗倔强的脑袋低垂下来。那条月经带成了我的救命恩人,它挽回了我的一只眼睛,然而我并不感激它,我想应怜要是能把我的心脏啄出来才大快人心呢,至少欧阳百惠不再用处心积虑地防备着我了,至少我不用千方百计地寻找跟上官清单独相处的机会了。可是事与愿违,死的不是我,而是应怜。
一些野狗突然狼一样没有声息地跟在了我的身后。当那些家养狗听到了野鹊们骚动不安的低声尖叫而狂吠不止的时候,那些野狗就停下来,警惕地四外张望。它们一声不吭,就像我在欧阳百惠面前一样保持良好的沉默,直到那些狂吠戛然而止的时候才又紧紧地跟上来。
我最终也没能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小卖部。
其实就算那个时候还有商店没有打烊,我估计我也没有勇气跟店员说我要买一包香烟。
事实上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发现镇东头的李老三小卖部还开着门的时候,我跨进门去为那些野狗买了几块猪大骨。
李老三从墨绿色的麻将桌前站起身给我称猪大骨的时候,望着我怪异地笑了。他说:“上官玉玲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买骨头?是你妈妈嫌饭要吃猪大骨了吗?”
李老三的问话让我想起那些馊味十足的难以下咽的食物。我说:“不是我妈妈嫌饭,是我嫌饭呢。”
李老三一下子笑呛了,鼻涕从嘴巴里喷出来,像大象的牙齿一样挂在嘴唇上。
我也笑了。
我说:“李大大你吐出象牙来了。”
我说完就抱着那几块骨头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了。
上一篇: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农民、农村干部的培训问题
下一篇:端 午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