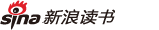作者简介:虽然,女,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在《黄河文学》《芙蓉》《长城》《大家》《福建文学》《文学界》《当代小说》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多个,另有散文散见于报刊杂志。
联系方式:河北无极县无新路五号石家庄实验中学(原无极师范) 李亚
邮编:052460
手机:13403214693
童年的雨
半夜里,一滴大大的水珠砸到眼皮上,我醒了。
叭叭!叭!又是几滴。下雨了!
奶奶咒一声“老天爷!”也坐起来,披上丹青偏襟褂子,从枕下摸出取灯,哧!手中升起一朵温暖橘黄的小花,小花移到壁内的龛台,点亮了洋油灯。
我坐起来,往上揪被头,被子湿了好几处,像印了数朵湿漉漉的花。
妈妈、小姑过来了,拿着塑料布和盆子。她们屋里也漏雨,但还是先来忙西屋的事。她们把被子枕头挪到八仙桌上,垒出一个窝,让我钻进去,苫上塑料布。又观察着屋顶往地上摆放盆。雨水连珠似的击打着盆子,先是叭叭大响,然后变成沉闷的咚咚声,水砸着水,溅起淡黄的水花。
我钻出脑袋,仰起脖子大叫:“哎!下雨啦!下雨啦!”
奶奶颠着脚趁过来,冲我额上拍下一掌:“祖宗!你个不解事的王八羔子!”
我向后一缩,塑料布就是一个透明的壳。雨打在上面,嘭嘭嘭嘭。母亲和小姑走后,奶奶在盆间串来串去,挪挪这个动动那个。她就着雨水洗净脸,又蘸水团起脑后那缕灰发,三挽两挽,挽出鸡蛋大一个髻。我趴在被堆里睡着了。
雨不停,我心内空落落的,围着被子坐在桌上,像个披袈裟的和尚,除了燕窝处多条小辫。小姑常抠着我的燕窝嘲笑:“燕窝深,绞介根。”在她眼里,我是个爱认死理的小子。其实哪能呢?她的对象奶奶看着不好,不肯让她嫁,我看就很好,她愿意的事就让她愿意了么!妈妈去城里看爸爸的戏,奶奶也不高兴。去城里看戏有什么要紧?城里毕竟比村里有趣。我脾气随爸爸,他让我翻跟头,见我翻得不成样子也就罢了,并没逼我硬练。我突然想起爸爸很久没回来了,他上回带来的石鸟,已经碎了三只,另两只找不见了,我想让他再带几只回来。
屋里处处雨味。盆里的水已倒过几次,又蓄了半盆子。雨水连绵得上不成房,若有可能,妈妈和小姑就到房上铺塑料布去了。这场雨,奶奶说是七年不遇,村里的坯房被雨泡着,已塌了许多间。人们都盼着天晴,天一晴,泛了潮的东西都要拿出去晒,不晒会很快长出白毛黄毛,比棉花毛还要细,潮乎乎的,一摁一个坑。
我从八仙桌上爬下来,躲着盆子来到门口。门旁两株对叶梅,开着绒腾腾的大红花,花芯结起高高的楼子,雨从瓦口冲下来,瀑布一样砸到花上。花们承受不住,左右乱摆,终于折了一枝。花朵耷拉下来,背面蓄满了水。我戴上草帽走出去,从墙角拿出一根带叉的杨树棍子,小心翼翼支起花来。
小姑在北屋卷挂历,她收集起几十个挂历,要一张张裁了卷起来,串成帘子。我进北屋时,她拿着一张图正看,是只熊猫抱着绿竹在啃。地上满着站不下脚,我千万小心还是踢倒了涂着黑漆靠墙放着的一排纸卷。小姑十分嫌恶地扭头瞪我:“你能不给我添乱吗?看你那脚,再踢一个仔细我怎么收拾你!”她这人脾气古怪,高兴了什么也让你玩,不高兴敢揪着我耳朵搡出去。我赶紧出去找妈妈,走到门口又踢飞了两根,一根飞得近,刚越过门槛,另一根远,飞到院子正中,落进一片水里。一个笤帚疙瘩紧追着我飞出来,没打着,我蹿出院子了。
大门南边一棵槐树下,有我家一个麦秸垛,垛上抹着一层黄泥。母亲头顶一个化肥袋子正弯腰掏引柴,她揪住湿麦秸往下一扔,掏呀掏,拽出一把干的。脚下雨水有红有黄,全是麦秸泡出的色。我家的母鸡曾钻进这麦秸垛下过多少个蛋呀!它还在里面孵出过一窝小鸡,昂首挺胸引着踱回了家中。水上漂着许多小船,全是妈妈抖落的麦壳。
我走回厨房,奶奶正从袋子里往外舀糁,说是要贴饼子。大雨的天吃什么呢?贴饼子就咸菜吧,新腌的小萝卜。棉花秸子也泛潮,妈妈折了几下折不断,整个插进灶里。我猛一拉风箱,灰烟腾腾喷出来,奶奶喊:“悠着悠着!你别让个孩子拉呀!”烟出不去,积在屋里,呛死人了。不如出去淋雨呢!
水顺着水道缓缓向外流去。
逢到下雨,大人最关心的就是院子能不能出水。早上起来妈妈蹲在出水口前,长竹竿子一阵捅,水才往外流了。大水滔滔,带走了碎纸烂柴、麦秸鸡毛。
我把化肥袋子的一角窝进去套到头上,立在门前看雨。街道成了河,河水哗哗向村中的大濠奔去。水面上冒出一个泡,越变越大,突然尖叫一声没了。旁边又冒出一个来,泡们眨眼间投胎变成另一个了。冒起的小泡灯罩似的,顶上旋着一点光,光里依稀有墙壁、房子、树、我,突然又全没了。
麻子爷裹着一块塑料布,捆扎得像个葫芦。他头顶草帽,一步一滑走过来。
“爷!去哪儿哇?”我站起来冲他喊。
他双手扎着,鸭子一样扭摆一下,险些滑倒。看清是我,找话说:“臭蛋啊,吃饭了没?回去吧,回去吧。街上有什么看头儿。”他冲我挥手。
我乐呵呵地说:“怎么没看头?下雨,打泡儿,王八羔子戴着草帽儿!”
他只顾往前走,没听见。如果听见了,他也许要两手一扣,夹起我的脑袋高高拎着,请我吃几个“胡萝卜”。
猪圈塌了,西屋塌了。猪捉了出来圈在院里,我和奶奶搬进妈妈屋里。
第七天上,雨终于小了,我穿上小姑的大黑裙子——得提到下巴处,才不至于拖地——跑到院里大叫起来:雨停了!雨停了!
我左右乱跳,跺出一片脚印。奶奶冲出来,一手扯我往屋里拽,一手照我屁股噼噼叭叭拍打。七天的雨让她想起六三年的大水,她愁眉不展,盘腿坐在炕上,搓着绳子一直叹气。
母亲和小姑的帘子快卷完了,我钻到她们中间,想拿张纸也卷一卷,小姑嚷起来,摁住我三下两下扒下黑裙子,剥得我只剩下裤衩。掺着红绳的小辫凉凉地贴到背上,激得我连打几个哆嗦。妈妈拿过她的水红褂子裹起我,让我坐到窗台上望爸爸能回来不。
窗户上原来有层毛头纸,冬天过后我一空一空打破了它们,没撕净的经受风吹雨淋,变得枯黄。我看见一只马蜂趴在窗户上,正一口一口叨碎纸,两只深褐的大眼睛,盛满忧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