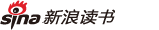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作者简介:黄厚江,1958年2月出生于江苏盐城,基础教育首批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二级教授,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国标本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主要编写者,省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省中语会副理事长,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
对中学语文教学有全面深入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教学风格、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系统的教学主张,倡导的“本色语文”和“语文共生教学”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获得三项省政府教学成果特等奖。发表论文数百篇,应邀在全国讲座数百场,执教公开课数百节,全国中语会等机构在各地组织“本色语文·共生教学”研讨会数十场。

出版《语文的的原点-本色语文教学的主张和实践》《语文教学寻真—从原点走向共生》等15部语文教学专著,以及学术著作《论语读人》,长篇小说《红茅草》获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提名奖等。
●内容提要:小说写了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个乡村少年的传奇经历。围绕他的经历展开了一连串曲折离奇、甚至有些荒唐的情节,也从一个儿童的视角表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现实。小说以乡村少年麻溜和小动物麒麟相遇、相知、互相慰藉和互相守护的传奇经历为主线,塑造了麻溜、美国在嘴子、麻雀子、月亮和胖桃等一批个性鲜明、经历各异的乡村少年形象,表现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复杂的成人世界陌生、茫然甚至有些抵制的心理状态,以及苏北里下河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反映人性复杂的同时,讴歌了人性的美好和淳朴,时代色彩鲜明,故事跌宕起伏,语言清新质朴,人物形象丰满。

●《红茅草》节选
24. 在大淖里发现了加宽的尸体
麻溜和妈妈还没有走到淖边,就听到那边人声吵嚷。远远地传来沈巧珍的哭声。
“死鬼啊!你这一走,害死了我啊!我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啊!”
麻溜和妈妈走过去,见已经到的人围成了一个圈子。见他们娘俩,人们分开了一条道。加宽头南脚北地躺在地上,除了脸和头,浑身都是泥,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两只手紧紧贴着身子,就像从下过雨的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有袜子,快要掉了,只有袜管还套在脚上。脸色煞白煞白,深凹的眼窝显得特别刺眼,以前总是显得忧郁的两个眼睛紧紧闭着。
雾还是很大,一阵阵怪兽似的从荡里边奔涌而出,迅速弥漫在人们身边。即使靠得很近,也看不清别人的脸。
沈巧珍瘫在加宽的头边上哭着:“死人哪,死人嗳。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到处跑什么?你这短命的鬼啊!你把我扔下来,叫我这日子怎么过啊?”哭声很是凄惨,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拖得很长,最后还要从喉咙里发出越来越细的含糊的声音,然后在喉咙里打一个嗝停住。哭完一句,就擤一把鼻涕,用力一甩,再把手在衣服的门襟上擦一擦。歇一会,再接着哭说。
麻溜妈妈一见加宽的尸体,也就眼泪千泷,想说什么又没有说。过了半天说了一句:“我这可怜的儿嗳,你怎就这样的死场呢。白发的老子白发的娘还在,你怎就半句话不留一撒手走了呢?”说着,已是泣不成声。
九佬他们几个人浑身是泥地站在一边。
“这人活在世上,谁不憋屈?像你这样,还不个个走这条路。”九佬抹抹手上的泥说,刚才是他在腰里捆了绳子让别人拉着去把加宽拔出来的。
“说来说去,他就是个迂子。可见,这书是害人的。”和九佬一起帮人家抬棺材的三宝说,“读书的人,就是想得太多。不像我们,有饭吃,有觉睡,什么也不想它。人活着,不就是个吃穿二字?”
“反正好死不如赖活。”
“你们几位,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好像我家加宽是自己寻这条路的?”沈巧珍听人们这样议论,停下哭泣抬起头说。
“你就少说句把吧!”麻溜妈妈制止她,“都这个时候了。”
“人都死了,还谈什么‘意思’?”尼赫鲁翻着白眼珠说了一句,他不知从哪来找来一张脏兮兮的芦席盖在了加宽的身上,但不够长,露出两只瘦长的脚,两个大脚趾长得特别刺眼。麻溜马上想到庄子上用来骂人的话:“滂流尸的!”“芦席卷子!”这些话说不上狠毒,有时候父母也用来骂淘气的孩子。谁也不会想到加宽这样老实的人是这样的结局。
有人给加宽爷打了电报。第二天他爷、他妈妈和他弟弟都从上海赶回来了,他已经出嫁的姐姐当天就都回来了。
他妈妈一回来就抱着加宽的身子哭得死去活来。
“苦命的儿啊!我知道你心里苦啊!你有苦为什么不对你娘说呐?我知道你是屈死的,是别人算计死的。你怎就一点音信不留,叫你爷你弟弟怎么为你做主啊?”
很显然,加宽家里人都怀疑,加宽的死和沈巧珍有关,甚至和癞忠武有关。可是却没有一点证据。但加宽的爷和弟弟加宏还是到公社里去告了状。公社里派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和大队里的民调干部八爹爹一起细细察看了加宽洗干净的尸体,说是只有额头有一点点擦破皮的轻伤,但不是致命的伤。其他没有任何伤痕,肯定不是别人害了他,是他自己夜里闲逛陷进了淖里的泥潭。
加宽妈妈和爷还是不肯放过沈巧珍,但也不知道如何处治她。就在收殓前的一天夜里,沈巧珍娘家来了人,悄悄将沈巧珍接回了娘家。
那天加宽入殓的时候,麻溜看到了金寡妇的三女儿金小三子,两只眼睛都哭红了。麻溜也觉得她长得真好看,心里想,加宽哥哥如果娶了她,肯定不会这么早就死。
25. 麻溜和麒麟的一次报复行动
这些天,麻溜一直像丢了魂似的。
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事情,能不能证明加宽哥哥的冤屈,更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别人。他怕自己说了也没用,而他确实也真说不清楚,因为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也奇怪加宽回去以后,家里怎么会那么安静;更奇怪为什么他半夜要走到淖里去。但麻溜心里相信,加宽哥哥的死,和白天赖忠文到他家里去一定有关。她相信,沈巧珍也一定知道。麻溜决定要采取行动,要报复赖忠武、赖忠文兄弟。
可是,怎么报复呢?他还没有想到主意。他想和美国嘴子商量,但这种事还是不告诉别人的好。当然,月亮更不能说。如果她一告三姑奶奶或者自己的妈妈和爷,一切计划都会落空。
晚上,他关好小院子的门,将麒麟放出来吃草玩耍。他没有心思和麒麟做游戏,任由麒麟从他身边蹦过来蹦过去。
融融的月光洒在院子里,非常宁静。屋后几棵大槐树的影子,浓浓的遮住小院子的一大半。麻溜仰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想心思。调皮的麒麟,总是一会儿来拱一拱他,一会儿来蹭一蹭他。也许它一个人玩太无聊了。过了一会儿干脆也依偎在麻溜身边不再动。麻溜用手摸摸它后脑勺的毛,便有点舍不得它。于是站起身来陪它玩。
“麒麟,冲!”麻溜一指槐树根下爷挑泥的泥兜,它就冲过去用头对着泥兜拱几下,扯几下,再衔在嘴里甩几下。
“麒麟,来!”麻溜一招手,它就几下蹦到麻溜的身边。
“麒麟,滚!”它就伏到地上,先向右边打几个滚,然后再向左边打几个滚。
“麒麟,翻!”它就把圆圆的鼻子先靠着地,然后一抬屁股一个前翻,一抬屁股一个前翻。能连续翻好几个。
“麒麟,拜!”它就把两个前腿抬起来,用两个后腿直立起来走路,两个前爪还合成作揖的样子,不停地拜。
“跳!”它就一蹦一蹦地向前,每次都能蹦好几尺远。
看着麒麟一个个机灵的动作,麻溜突然有了报复癞家兄弟的主意。他为自己的想法很得意。
很快,机会就来了。
那天下午,麻溜正在地里薅秧草,听到大队的大喇叭里很兴奋地在喊:“广大社员请注意!广大社员请注意!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公社放映队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大队放电影。请广大革命群众晚饭后到大队部的广场上看电影。”
“是个好消息!”麻溜自言自语地说。
对何淖庄的年轻人来说,一年来一次的公社的电影船带来的是过年之外的最大的快乐。一得到消息,大家就开始兴奋。挑泥的不再觉得泥担子沉重,割麦的会觉得镰刀像刚磨过一样锋快。大家都在心里盘算着晚上和谁一起去,和谁坐在一起。有人已经约好了平时没有机会见面的情人在电影场之外的哪个地方幽会。甚至有人高兴得不敢相信:“不可能!肯定是有人撒谎骗人的。”直到有人指着大队部门口广场上已经树起来的一丈见方的白色大屏幕,不敢相信的人才心里踏实:“嘿嘿。看来是真的要放电影了。”大家远远地看着两根竹竿上挂着的方方的大银幕,恨不得太阳一下子就掉下去。大家互相打听着电影的名字,是不是打仗的电影,有没有看过。那时候,大家都不关心电影的演员,只关心电影的名字和内容,甚至只关心内容,连名字也不关注。看过之后,就是说:“今天电影真好看。——从天一直打到尾。”“他妈的小日本鬼子真坏!”“国民党就是不经打!”
太阳还没有落山,就有孩子光着上身,穿了一件手工做的大裤衩,搬着凳子去抢占有利的位置。有的人拎着一张小凳子,有的扛了一条长凳为一家人占位置,也有的一个人搬了几条凳子为别人抢占位置。放电影的人先在打谷场合适的地方挖个坑树一根杆子。在杆子前摆一张八仙大桌子。放映机便都摆在桌子上。在桌子的正前方树两根杆子挂上荧幕。于是桌子前和荧幕之间自然便是最好的位置。先来的人便占领这一块地方。来迟的人,有的就坐在前面的地上,有的则站在坐凳子的人后边,再后边的人就站在凳子上,甚至有人就坐到荧幕的反面。太阳一落,人群就吵吵嚷嚷地从四面八方的小路上赶过来。人越来越多,小路上就挨挨挤挤,有时候为走路也会闹出矛盾,甚至在过桥的时候有人挤得掉进了河。本大队的人,除了身体不好的,除了年纪特别大的,除了有特殊事情的,大家都不会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邻村的人也会赶过来,有的人为了看一场电影,能跑七八里地,有的人能连续几天赶到邻近的七八个大队,同一部电影看七八遍。
平时麻溜总和他的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电影。他们一般不会搬凳子,因为他们很少坐着看。电影开始前,他们都会到处逛荡,看看有什么热闹可看。因为看电影也是各个庄子的年轻人展示实力的时候。遇到互不服气的,则要比试一番。但那是很君子式的比试,很有古人交战的风度。首先要说好是摔跤还是打拳。一般都是一对一,双方都不会乱来。更不会有人暗中下黑手,或者一拥而上。麻溜是少年中的高手,只要他从电影场上走过,就有人在背后指着他小声说:“那是麻溜。”麻溜装着没有听到,身边的伙伴们便非常自豪,摆出很得意的架势。一直到幻灯片和新闻片放完正式电影开始,他们才会找一个地方站下来看电影。如果电影喜欢,会安安静静地把电影看完。这时候月亮会让麻溜坐在自己的小凳子上。凳子不大,两个就挤一挤坐。美国嘴子他们会在后边做着鬼脸。可麻溜一回头他们就不敢了。月亮说不用看他们。如果电影不是自己喜欢的,不是打仗的或者打得不激烈的,他们就会不再看。电影不看了,他们或者就在电影场四周闲逛着,或者就会找一个地方练习摔跤打架,有时候会吸引很多人来围观。也有时候他们会搞一些恶作剧。有一次,他们几个人提前离开电影场。不知谁的主意,学习电影里游击队的做法,将电影场四周的几个桥的桥板都掀进了河里,说是“把鬼子困死在电影场上”。电影散场之后,很多人都找不到回家的路怎么走,也有的绕了很多路才回到家。后来知道麻溜参与了这件事,爷便认定是麻溜带的头,用栽秧用的湿漉漉的绳子狠狠抽了麻溜的屁股。麻溜知道自己不该做这样的“缺德事”,也记得不是自己的主意,但他只是忍着,坚决不说是谁的主意。
这天晚上,吃了晚饭,麻溜和美国嘴子两个人一起去电影场,而且是等庄子上很多了已经走了才从庄子上出发。美国嘴子知道,麻溜自从挂过牌子之后便不愿意和很多人在一起。胖桃、麻雀子和五子他们也都不再来找麻溜。等他们到电影场的时候,人基本到齐了,已经在放幻灯片。方桌的周围和前面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人。方桌后边的那根竹竿上高高挂着的电灯泡放着十分耀眼的光。一群一群的飞蛾和虫子在它周边盘旋,不时有飞蛾和虫子撞在灯泡上或者竹竿上“啪”的一声落到地上。麻溜和美国嘴子悄悄来到电影场上。
“要找个地方坐下或者站下来吗?”美国嘴子问。
“不用。兜一兜再说。”
于是他们便绕着电影场人群的外围兜了几圈。麻溜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癞忠武、癞中文的儿子和女儿,便说:“找个地方站下来看吧。”他们便在人群中挤出一条缝站定下来。那天放的电影是《智取威虎山》。等到座山雕和杨子荣开始对暗号的时候,麻溜说肚子疼,提前离开了电影场。美国嘴子要陪他一起回来,麻溜说,电影好看,你看了讲给我听。
于是麻溜一个人溜回了家。他抱着麒麟来到一块玉米地里,伏在一条小路的边上。这是癞忠武和癞忠文家的几个孩子看电影回家必须经过的地方。麻溜找到了白天看好的位置。那里堆着一堆他白天弄来的细沙土。麒麟显得特别兴奋,不时用舌头舔一舔麻溜的手,舔一舔麻溜的衣服,有时候还舔一舔麻溜的脸。一对圆圆的眼睛闪亮闪亮,骨溜溜地打转,总是盯着麻溜看,似乎想知道今天带它到这里来做什么事。
看着麒麟兴奋的样子,麻溜有点犹豫了。
本来他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最好的主意。他为自己想到这样一个好主意感到得意。但他现在觉得这样做对不起麒麟。前一段日子,癞忠武曾经让民兵班白天黑夜地捉鬼,可自从加宽死了之后,明显放松了许多。白天几乎看不到小六子他们几个人到处转悠了,晚上也是装装样子而已,兜个两圈就回家睡觉了。如果因为今天晚上的事,让麒麟暴露了怎么办?麻溜知道,癞忠武肯定能够将今天的事和前一阶段闹鬼的事联系起来,再一次大张旗鼓地捉鬼。肯定会让民兵班成天成夜地四处捉鬼的。当然,他们不知道是麒麟,他们只知道是“鬼”。但那样对麒麟很危险。
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麻溜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仅仅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找美国嘴子他们肯定也不行。自然也不能告诉月亮,如果她告诉了妈妈,计划就破产了。而且麻溜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麻溜觉得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哪怕是美国嘴子。但是如果不报复癞忠武、癞中文,麻溜无法甘心。加宽哥哥那双深深凹下去的眼睛始终在他眼前。他想起下雨天他和加宽两个人躺在加宽的床上看着屋顶的篱笆,他想起加宽教他读诗情景,他想起加宽进城为他卖回来的橡皮筋,……
也只能这样了。麻溜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把麒麟揽在怀里。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保护麒麟,绝不能让六子他们捉到麒麟,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麒麟。
不一会儿,电影结束了,电影场上传过来一片喧嚷声。天空中晃动着手电筒的光柱,人群很快分散到电影场四边的各条路上。渐渐地电影场上不再喧闹,灯光也渐渐熄灭了。看电影的人已经淹没在黑色的田野中。一开始人群都是一队队的,然后再不断分散。一起走进庄子的是一大队人群,进了庄子之后便分散到一条条巷子里,不断有人进了自己的家门。癞家兄弟是住在庄子西南角上的几家零散户。当初他们弟兄分家时,庄子里还是有起屋的墩基的,但他们为了养鸡养羊更方便,就在庄子西南边的朴刀匡地里选了墩基造了房。那块地就像一个半岛,三面是河,一面有一条路和庄子紧连着。路的两边都是玉米地。麻溜和麒麟就埋伏在路边的地里。
癞忠武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癞忠文才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才几岁。姊妹三个看了电影便一起回家。在庄子边上和大家分开之后,姊妹三个便沿着那条路向自家的墩子走去。出了庄子,田野显得特别黑,特别静。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是癞忠文的儿子,一下子离开了人群,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姐姐,我怕。”说着便蹲下不肯走。田野一片寂静,不知名的虫子偶尔发出几声鸣叫。远处有灯光在天空闪动,萤火虫在庄稼地上飘忽。
“锁子,不要怕。你看,已经看到我们家的灯光了。”
锁子抬头一看,真的看到自己家中的灯光了,于是站起来身又向前走。
突然,右边的地里传来一阵恐怖的怪叫,有点像被卡住了喉咙的牛,又有点像挨宰杀的猪,声音低沉,尖厉。
三个孩子都停住了脚步。四周一片死寂。
过了一会儿,三个孩子又手拉手轻轻抬起脚步向前走,那怪叫声突然又响了起来。三个孩子的脚步又停了下来,都蹲在那里不动。突然,哗的一声,在他们的头顶落下一片沙土。接着又是哗的一声一片沙土,过一会又是一片沙土。中间还夹杂着一声声刚才那种怪叫。
三个孩子吓得蹲在地上,一动不动。可是接着什么动静也没有。就在他们准备起身再向前走的时候,一个小怪物从玉米地里蹦到他们的面前。三个孩子哇的一声都哭出了声,就连癞忠武家最大的女孩子也哭了起来。只见那小怪物一会儿四条腿走路,一会儿两条腿走路,一会儿翻着跟头向前,一会儿在地上打着滚,路边的玉米地里也发出哗哗的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很快地穿过。
三个孩子哭成一片,惊恐的叫声,在晚间的田野里显得很是恐怖。一会儿,那小怪物已经看不见了,只是偶尔还有一两声怪叫。可三个孩子还是不敢再走,就蹲在路边喊着爷和妈妈,大一声小一声地哭。癞忠武老婆可能是看到孩子没有回来不放心,也可能是听到了孩子的叫声,从家里找了过来。问了情由,见癞忠文的儿子吓得眼睛发直,赶紧把他抱在怀里,一边用手指在地上粘一点土,涂在孩子脸上,一边嘴里念念有词:“锁子不怕,锁子胆大!锁子不怕,锁子回家和妈妈睡觉。锁子不怕,锁子胆大!锁子不怕,锁子回家和妈妈睡觉。哦,锁子回家和妈妈睡觉了。”然后抱着这孩子,带着另两个孩子向家里走去。那两个孩子还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着。
“夜里走路,不要回头看。越看,越怕的。人的肩头有两盏灯,鬼看到这灯是怕的。你一回头,这灯就熄了。”
她这一说,两个孩子更加害怕,拉着她的衣角紧紧跟着,一步也不敢拉下。
看着癞忠武老婆搀着三个孩子走回家去,麻溜心里觉得少有的痛快。他搞过无数次的恶作剧,可是他觉得这一次和以前任何一次都不同。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情。或许,这才真正是拐子爹爹说的“伸张正义”。而且他决定这件事要永远不告诉任何人。有些事情是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做,也只能自己一个人知道,麻溜想。
天上没有月亮。稀稀拉拉的星星,在远远的天边向他眨着神秘的眼睛。他看看麒麟,麒麟也正抬头看着他,对着他眨着那孩子一样的眼睛。它似乎还很兴奋,也很开心。麻溜把麒麟抱在怀里,用头抵着麒麟的头,用鼻子抵着麒麟软乎乎的大鼻子。“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他轻轻拍拍麒麟的软乎乎的鼻子。麻溜觉得从天开始,麒麟不仅仅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而且是他要好好保护的人。如果麒麟受到伤害,那就是自己的罪过。那是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26.孩子被吓,癞忠武再次组织民兵捉鬼
赖忠武和癞忠文的儿子被鬼吓出病来的事情,很快就在庄子上传开了。
不仅是小脚五奶奶,很多人都相信庄子上又开始闹鬼了。本来加宽的死,就有人说是鬼把他搀进了淖里。现在三个孩子亲眼所见,于是鬼的事越传越像,越传越真,甚至有人建议请个大神来庄子上除妖。
“这鬼也太胆大了!居然敢吓唬民兵营长的孩子!”也有人私下里说着风凉话。
但癞忠武并不相信是鬼。
“请什么大神来除妖!那是牛鬼蛇神!那是封建迷信!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从来不相信这一套!”他决定一定要抓住这个“鬼”。
他又把武装民兵班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训话:“什么鬼不鬼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信鬼的!我们敢与人斗,敢与天斗。与天斗,就要与鬼斗!与鬼斗,就是与人斗。这一次,我们要加强力量捉鬼。一定把鬼抓住!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以六子为首的几个民兵斗志昂扬,回答“有”的时候,六子还把那把步枪举了举,就像真的要上战场一样。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强大的。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勘察过现场。现场的脚印说明,那应该不是鬼,那是人。因为鬼是没有脚印的。是有人在背后操纵着这鬼。”
他没有说完,下面几个民兵就开始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看来他们是不怕鬼的,但似乎有些怕人。
“有人,大家更不用怕。大家相信,阶级敌人总是一小撮。他们是见不得阳光的,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破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大家有什么害怕的呢?”
“不是说看见了四条腿的怪物么?”民兵中的大兔问。大兔说完话,还吸溜一下嘴唇,他的嘴有点像兔子。
癞忠武的确看到了四条腿的动物的脚印,而且他反复研究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脚印。但他没有把这些告诉民兵们。
“大兔,你害怕不害怕?你参加不参加?你害怕,你不要参加,明天还去挑河泥。”癞忠武很平和地问。
“我参加!我不怕!”大兔说着,还把左脚跟和右脚跟靠一靠,两只脚垫了垫,尽管那双黄球鞋要是不用绳子扎,鞋底就和鞋帮就分家了。
大家都知道站岗巡逻肯定要比挑河泥轻松,挑着两粪桶污泥在水田里走,可不是个轻松的活。而且参加了这样的任务,说明政治上是可靠的,也说明自己是受到癞忠武信任的人,将来有个什么事情要和癞家打交道就好说话多了。
接着癞忠武就布置如何站岗,如何巡逻。都是和上次差不多,就是强调白天夜里都不能有一点放松。
麻溜伏在学校的围墙上,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
27.麒麟忽然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麒麟竟真的不见了。
麻溜想都没有想,就去找美国嘴子。美国嘴子正在打摆子,睡在床上,身上盖着两条被子。
“麻溜找金贵有什么事?”
美国嘴子的妈妈问。金贵是美国嘴子的大名。
“没什么事,看看金贵,五妈。”
美国嘴子和麻溜平辈,他爷排行老五,麻溜就叫他妈妈五妈。
等美国嘴子的妈妈去地里拔菜,麻溜用手拨开美国嘴子差不多蒙在脸上的被子,说:“麒麟不见了。”说吧,两眼紧紧盯着美国嘴子。
“什么?麒麟不见了?”美国嘴子忽地拗起头,很快就把半截身子钻了出来,“你以为是我?”
“其他没有人知道。”麻溜说着,仍然盯着美国嘴子看。窗户很小,隔墙板上都熏黑了,房间里很暗。美国嘴子的脸上蒙着一层灰色,额头上有渗出的汗,眼睛显得很没有精神。
“我肯定没有说,没有对任何人说。”美国嘴子看着麻溜的眼睛说。
“我相信你。”麻溜本来以为一定是美国嘴子告诉了谁,不知什么原因,现在他相信他没有告诉别人,“你躺下吧。刚刚开始出汗。”
美国嘴子躺下了,干咳了两声,说:“你再想想,还有谁知道。”
“难道是我爷?”麻溜说。
“他晓得?”
“他晓得。”
那是美国嘴子看到了麒麟之后的第二天晚上。
半夜里,麻溜又悄悄起床,来到小院子里,关了院子的门,把麒麟放了出来。麒麟吃了草,在小院子里撒欢。一会儿蹦过来,一会儿又蹦过去,一会儿在麻溜前面用鼻子蹭蹭他的脚,一会儿在他后面用头拱他的脚后跟。麻溜正想用两只手搭着它的前腿,让他用两只后腿走路,只听树棍门吱呀一声。麻溜一掉头,是他爷披了衣服站在他身后。
“他们要抓的就是它?”爷问。
“嗯。”麻溜用哀求的目光看着爷。
“癞中武家的几个细的是你吓的?”
麻溜不说话。
“让它去吧。留着会惹祸的。”
“他们会,会打死它的。”
“你留不住的。”
麻溜不说话,看着他爷。
月光很不明朗,在爷的脸上留下一片影子,麻溜看不见爷的眼睛,连爷脸上的神情也看不清。爷走近看了一会麒麟,用手托起麒麟的下巴,盯着麒麟的眼睛看了看,麒麟也不陌生,任由爷摆弄,像是很熟的样子。
“倒是个灵物。”爷说,“早点睡。”说罢,也进屋困觉去了。
难道真是爷出卖了麒麟?麻溜问自己。
美国嘴子将自己的被头在下巴下塞塞紧,可能是刚才折腾了一下,他浑身发抖:“会不会麒麟自己跑了?”
“不会。”一发现麒麟不见了,麻溜就这样想过。可是他看了,那么大的树根,麒麟拱不开的,再说,这么多天,麒麟也没有想出来过,而且那树根离开洞口那么远,肯定是有人搬开的。
晚上吃过晚饭,趁爷上茅缸的时候,麻溜走过去,说:“麒麟不见了。”
他爷吃了一惊:“什么麒麟不见了?你不是——”
“是那个麒麟,是……”
他爷明白了:“留不住的。不要惹事。”
“它哪里去了?”
“让它去吧。”
“它哪里去了?”
“让它去吧。”
爷不再说话,吧唧吧唧地抽着烟,烟头的火很快活地跳,爷用大拇指头按了按红红的烟锅,又接着吧唧吧唧地抽。
麻溜不再说话,也不洗脚,一个人跑到厨房屋北头的小房间的粮柜上,拉了一条被子蒙着头躺下。妈妈叫他洗洗脚,他装着没有听见。
过了一会儿,爷来了。又装了一袋烟,一边吧唧吧唧地抽烟,一边说:
“人不能充雄。能挑八十斤,就挑不了一百。”麻溜什么也不响。
“这世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爷年轻时候,也不是怂人。”吧唧吧唧,烟锅里的火一闪一闪……
“谁不想做点事情。——结果,你看,连累你哥兵都当不成,想学个木匠,也不让,只能自己在家里瞎捣鼓。——欠了多少人情才算同意了。”麻溜还是什么也不响。又是一阵吧唧吧唧。烟锅里的火一闪一闪的……
“你人小,可爷知道你心雄。”吧唧吧唧。烟头红红地闪。麻溜还是什么也不响。
“可世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爷年轻时候,也有过一番雄心,最后……——让它走吧。它自有它的命……”
麻溜还是什么也不响,爷以为他睡了,就自己回屋子去睡觉。
第二天,大人们都出工了。月亮来了,她告诉麻溜,麒麟果真是被爷送走了。
“麻溜,你最近干坏事了吧?”月亮一来就问。眼睛瞪得圆圆的,像圆圆的月亮,但像审讯犯人似的盯着麻溜。麻溜第一次发现月亮的睫毛这么长,就像是假的。麻溜说:“月亮,你的睫毛是假的吧?”
“别打岔!你听话不听话?你不听话,重要的事情我就不告诉你。”月亮说,眼睛又变成了弯弯的月亮。
于是麻溜就告诉了月亮遇到麒麟的事,吓唬癞忠武的几个孩子的事,还有麒麟的所有事,并且叮嘱月亮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我就知道一定是你!——怪不得你们家小院子里最近不大正常。”月亮说,“那昨天晚上三舅舅送走的一定是麒麟。”
“什么?你看见了?”麻溜急切的问。
于是月亮告诉麻溜,前天半夜她妈妈肚子不舒服,她去找陈良医,在路上遇到了麻溜爷,怀里抱着一个东西,一身的斑点,像狗又不是狗,像羊又不是羊。月亮估计是麻溜弄回来养的什么东西,他爷不让他养在家里就送走了。
知道是爷送走了麒麟。麻溜真的很生气。

28.麻溜爷是个能够怕事的人
都中午了,麻溜还没有起来。麻溜在生爷的气。如果是往常,爷早就掀了他的被子:“太阳都嗮到屁股了!还不起来?”说不定还照着屁股就是几个巴掌。可是今天爷就像不知道麻溜还没有起来。
麻溜从小就怕爷。
因为调皮惹事,麻溜经常挨爷的打。小错误,瞪瞪眼;大一点错误,一个葱根(用巴掌拍头的后脑)打过去,或者一脚屁股。再大一点的错误,就用绳子抽。庄子上,每个爷都打孩子。但人家用棍子打,随手一根树棍或树枝,抡起来就打。但麻溜爷从不用树棍或者树枝,他总是用绳子,打哥哥是这样,打麻溜也是这样。爷从来不打姐姐。姐姐是女孩子,姐姐又很乖,从小身体又不好。麻溜挨打最多,因为麻溜调皮,总是闯祸,还因为麻溜挨打从不花招,不认错。只要自己错了,麻溜任由爷打,不躲,不哭。如果他认为自己不错,他就会反抗。
但麻溜知道爷喜欢自己。爷一直跟别人说麻溜像他。爷进城总是带着他。那时候要节省一点粮食进城卖掉,家里作其他用处。爷总是天蒙蒙亮就挑着粮食进城,也总是让麻溜跟着。
爷的身材不是很高大,不像麻溜的大伯。但干农活是个难得的好手。堆草堆,占粮食,扬场,全大队都闻名的。他堆的草堆,又大又圆,几个人一起把草送到他脚下,草在他的铁叉下是那么柔顺,服服帖帖。草堆于是越堆越高,他自己也渐渐高起来。麻溜在下面看,爷就像站在云里边。让麻溜想起一首儿歌:“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吃袋烟……”爷堆的草堆总是又圆又高的,而且样子好看。所以麻溜很得意。最让别人佩服的是麻溜爷堆的草堆下雨天不漏,而且样子还是那样好看,像个宝塔,也像个蘑菇。生产队里的大牛皮总是不服气,可他堆的草堆一下雨,顶子就陷了下去,四周不潮,中间都是烂的。麻溜爷堆的草堆顶上就像是屋子的顶,滑溜溜的,每根草都是顺着的,水总是顺着麦秸或稻草淌到了地上。
何淖庄的人都知道:“女人的肩,男人的锨。”意思是,看一个女人是不是能干,就看她能不能把一个褂子的肩补好;看一个男人是不是能干,就看他会不会扬场。麻溜爷扬场那更是没有人不服气。——扬场就是用木板掀把稻子或麦子抛上天空,借助风把干瘪和饱满的稻子麦子分开。——他一抬头就知道是多大的风,该使多大劲就使多大劲,该向上风迎多少就迎多少。等他扬完一个麦堆或稻堆,那地上一层一层,清清楚楚,最上边是土块瓦砾,然后是饱满的麦子稻子,下边是干瘪的麦子稻子,最下边是草叶和麦芒。
麻溜爷也是队里育秧苗的好手。育秧是生产队里非常重要的事,影响这一个秋季的收成。育不好,秧苗不够,就要花钱到外队去买,甚至要到外地去买,如果买不够,水田就要荒着,只能重新晒干,种种黄豆之类辅助作物。因此,从选种到浸种,从上窝到出窝,从做秧池到秧池的管理,一个环节也大意不得,随便哪个环节都可能使秧苗遭灾。种子上窝之后,是不能离人的。爷经常带着麻溜睡到焐稻种的队房里。夜里爷都要起来好几次,从来不用闹钟。手伸到稻种里一探,就知道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高了掀开上面覆盖的稻草,凉一凉,冷了洒一点温水。而水温爷一伸手就知道。
麻溜爷挑担的力气不是最大的,但挑担的样子非常好看。看上去总是很轻松,轻轻晃悠的扁担,轻松的两腿和脚步,以及微微晃动的身体,是那么协调放松。爷挑担的号子,也是轻轻的,悠悠的。不像有的人挑担,总是显得很吃力,好像随时就要扭了腰,就像扁担随时就要断了似的。那号子更是难听。麻溜最爱看爷换肩的动作,肩膀头轻轻一抖,担子就从右肩换到了左肩,轻轻一抖,就从左肩换到了右肩。麻溜想,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像爷这么能干的农民。
进城之后,爷找一个僻静处,将粮食担子放下,让麻溜看着。他自己在一只小淘米箩子里放上一点米,到河码头去,装着淘米的样子,和那些早起淘米的城里主妇们谈卖米,谈妥了,就带他们过来秤米付钱。爷和城里主妇们秤米算账付钱的时候,麻溜就会在巷子口两边张望,看有没有工商所的人。爷总是用眼神夸赞麻溜的机灵。
庄上人老一辈人都说爷当年也是个人物。拐子爹爹就说过,你爷当年是方圆三十里第一个龙师傅。只是如今不兴这个,如果当初……。当初什么呢?麻溜问,可是拐子爹爹就不再接着说。“你爷这个人,是个能人,可就是少那么一个气。”过了一会儿,拐子爹爹又感叹了一句。什么是气呢?不便不再说。麻溜也不再问。
舞龙是这一代非常重要的活动。每年过年总要舞上个把月的。这一代,大多数村庄以前都有一条龙的。如果一个庄子,连条龙也没有,这个庄子就会被邻村瞧不起,庄子上的人也没有面子,到邻村去看,还会被邻村人讥笑。
第八营是一条青龙,是九个人的。隔壁的李家墩子是一条白龙,是七个人的。离五里地远的蔡家墩子是一条黄龙,是十一个人的。这一代的龙和别处有一个不同,就是总有一个拿龙釢的人。龙釢就是在一个直径不到一尺的球状的架子外面包上红布。在这个红布包的球中间穿一根能转动的轴,将轴两头装在一个铁叉子的两根杈头上。铁叉子接一个二尺来长的木柄。在木柄和铁叉头相接的地方会套几个金属的圆圈。龙师傅挥舞着这龙釢指挥着龙舞龙的人。一抖手中的龙釢,金属的铁圈就像铃铛发出响声,既引起舞龙人的注意,也引起看舞龙的人的关注,而且还渲染了气氛。舞龙头的人要始终将龙头的嘴巴追赶着龙釢,似乎总想一口将龙釢吞了。而龙师傅不仅要用龙釢引着龙头,舞出好看的花式,而且要指挥整个龙身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什么跳龙门,什么捆龙索,什么十八滚,什么金龙翻身,什么金龙脱索,什么金龙如海,有几十个套路,上百个招式。而要表演什么套路,出什么招数,全看龙师傅的挥舞的龙釢。麻溜最敬佩拿龙釢的人。
每年过年的时候,几个庄子的几条龙会聚到一起斗龙。那是过年的一次盛会,参加斗龙的庄子上的男女老少都会来。斗龙,一是看谁家的招数多,谁先没有了招,谁家就输了。最见功夫的,是几条龙由一个龙釢指挥,同一个指令,有的做得出,有的做不出。做不出的,自然就输了。比如,龙师傅龙釢一摇,做了一个动作——捆龙索,就是要把龙身打成一个复杂的结,就像是龙被一条绳子捆住了;龙师傅龙釢再一摇,做了一个动作——金龙脱索,就是要把龙身子打成的结一下子打开。技术不娴熟的,有一个人出了差错,就会一片混乱,总是打不开来。这个时候拿龙釢的,当然是公认套路最多、招数最多、最有权威的龙师傅。麻溜爷就是大家公认的龙师傅。可是麻溜没有怎么看过爷舞龙的样子,记得只看过一次,那时候还小,几乎没有印象了。后来就看不到了。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麻溜觉得爷一点也不像别人传的那样,甚至不像自己小时候觉得的那样。除了生活做得好,真的什么也看不出。而且显得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什么话也不肯说,总怕得罪人,还经常责怪妈妈会多事。
麻溜这样胡想着,妈妈进来了。
“不要怪你爷。起来吃粥有事情。”
麻溜转了一下身,还是没有起来。
“起来吧。你也不是细小的了。——”妈妈似乎有点生气了,接着又语气软和地说,“你爷最近很烦的。——不要再为难他——”
麻溜忽然想起最近家里气氛和以前有点不一样,妈妈和爷总是在房里很审美地小声叽咕着什么。游神有一次还钻进爷和妈妈的房间说了很长时间话。他临出门的时候,妈妈跟在后面谢他。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要说什么谢!所应,你们自己当心。我也是有半句没半句听到的。真不真,你们自己映当映当。”说完了,就一溜烟的走了。
难道爷真遇到什么事了?麻溜又想起麻雀子爷阴狠地说的那句话:“我是反革命。你老子是什么,回去问你爷!”
“爷到底是什么?”
“没有什么事的。听说有人想揪你爷的尾巴。——”
上一篇:王传宏: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主奖获得者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