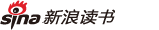●作者简介:王传宏,女,江苏东海人。现任教于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市作协签约作家,曾获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主奖,2015、2016年上海市作协优秀作品奖。著有长篇小说《诱惑》《疼痛》《我走了》,先后在《收获》《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等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中篇小说《谋杀》被改编拍摄成电影《春花开》,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

●内容提要:小说讲述了一群混在日本的中国人。
中专生别小诺因少女时代的一次意外失身而失学。在故乡小镇,别小诺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女人,不得不远走他乡,最终通过婚介所远嫁日本。然而等她来到日本后,却发现自己从未谋面的丈夫森村浩一竟莫明其妙地消失了,屋子里除了一些生活用品,还留有几张日元钞票。不久,别小诺不得不走出家门,独自面对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为了生活,别小诺吃过许多辛苦,直到意外遇见许多年前那个让她的生活陷入无尽麻烦之中的男人巫加越。
巫加越当年去学校调研时,与还是一名学生的别小诺相识,并有了肌肤之亲,后却一走了之。已是人到中年的巫加越,离婚后去日本淘金。在日本,他从最底层的清洁工做起,与妻子纪小敏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拥有自己的事业。然而巫加越却因身陷赌博泥沼而欠下巨额债务,最终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小说中的另一条叙事视角是属于别小诺的同事、留学日本的年轻女人马寄南的。马寄南因父母超生,一出生便被寄养在亲戚家。后虽被接回上海家中,却几乎成为漂亮姐姐的一个影子。长相普通的马寄南从小在被冷落与忽视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又追随姐姐来到日本。但她对理想与爱情的执着追求,使她的生活充满了许多不可知的变数。马寄南最终决定回国,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与新生活。
别小诺仍然在日本继续等待着。周末下班的时候,别小诺发觉门没有锁,她以为是自己一时疏忽忘记锁门了。可是屋子里的灯是开着的,卫生间里传出哗哗的水声,有人正在里面洗澡。难道是森村回来了?!别小诺倚在墙上,身体顺着墙壁慢慢往下滑,终于一屁股坐到地上……
第二章
别小诺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穿过前门的玻璃,落在她的枣红色绣花棉袄上。别小诺揉了揉眼睛,顿时清醒过来。她睁着眼睛在地板上躺了很久,依然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整个旅程显得出人意料的短暂,几乎与自己骑着自行车从小镇到市里买什么东西差不多。在没去之前,已经计划了很久,那要买的东西是如何如何好,又是如何地必不可少。这样的想像在出发之前终于变成了一股急不可耐的热情,于是用力蹬着自行车,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东西买到手。但等到了之后却发现,连日里培养起来的热忱忽然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别小诺低着头看着那要买的东西不相干地躺在冰冷的柜台里,忍不住有些疑惑起来,自己火急火燎地往这儿赶,就是为了这么个平淡无奇、十分不起眼的东西么?
别小诺慢慢地起身、洗漱,开始整理自己随身带来的东西。别小诺发现,屋子里的东西虽然简单,却大都实用而顺手。等到她把两只大旅行袋里的东西整理好,屋子里的一切看起来便显得顺眼多了。别小诺用冰箱里的东西给自己做了一顿早饭,然后便坐在那里低着头想心事。
别小诺忽然觉得,森村或许只是临时有事离开了。要不,他怎么会给她留钱呢?至于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离开的消息事先告诉她,她想了想,觉得那只是因为二人语言不通。或许,森村曾经把这消息告诉过婚介所,可是别小诺那时已经上了飞机,婚介所已经没有办法通知到她了。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别小诺现在能做的,只是耐心地等待。一想到这里,她的心情便渐渐变得明朗起来。
信封里的钱别小诺早就数过,共有十万日元。她把它换算成人民币,看起来似乎也不算太少。虽然别小诺早就知道这里的物价昂贵,但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却是一无所知的。根据森村留下的钱,别小诺觉得他离开的时间应该不会太短。虽然她有些担心,要是她出去了,而森村却在这个时间回来了怎么办?可是,一直在这里枯坐着似乎又有些傻。下午的时候,别小诺决定出门转转。
外面的阳光很灿烂,别小诺站在阳光下,忍不住仰起脸闭上了眼睛。阳光在脸上的感觉似乎是有重量的,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家很远了,心里不禁涌出一丝感伤。门前的小路静悄悄的,看起来既陌生又神秘。别小诺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虽然到处都有房子,她却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偶尔能看见有老太太站在门前弓着身子晾衣服,见别小诺打量她,便又转身回去了。而当老太太退回屋里之后,那房子似乎又变成死寂一片,几乎不像是有人住在里面。别小诺还记得那个老太太看她时的眼神,虽然只是匆匆瞥了一眼便迅速将目光移到了别处,但那目光中的惊异却让她的心里忍不住一噤。
每一所房子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模样,既安静又诡异。别小诺虽然十分好奇,却不敢在它们面前多加停留。或许,在每一扇屋门背后都有一双像那个老太太一样的陌生的眼睛在看着她。别小诺忍不住有点惭愧起来,她原本是想探究别人的生活,没想到却早已被别人好奇地打量了。
别小诺很快便在附近找到了超市和菜场,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门面很小的邮局。别小诺在邮局给母亲写了封报平安的家信,又在超市买了几样零碎东西。超市的收银员一边收钱,一边唱歌似地说了一长串的话。别小诺虽然尖起耳朵认真分辨,却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接下来的几天,别小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闲逛上。周围都是普通的景致,但是所有的一切在她的眼中却是那样的新鲜有趣。路边的便利店、点心铺,只能站着吃饭的卖便当的饮食店,甚至里面没有人、只是摆着几台机器的自动干洗店,她都忍不住要好奇地看上几眼。在每一家店铺,别小诺都要消磨掉好长时间。但是这些商店大都很小,里面常常只有她一个顾客。这又让她忍不住觉得有些难堪,不好意思在里头逗留太久。围着围裙、包着素色头巾的女人微笑着向她打招呼,别小诺并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只是点点头,赶紧离开了。
路上的行人乍看上去,除了衣着更整洁时髦一些,似乎与家乡小镇上的人没什么二样。但是别小诺仔细打量之后却发现,那是完全不同的二种人,就连长相也毫无相像之处。那是一张张由文明的精致与旷野的古拙微妙揉合之后的面孔。每一张脸都是沉静冷淡的,却会忽然之间微笑起来。从脸上几乎什么也看不出,就连不满和嫌恶也被礼貌的微笑遮掩了起来。只有两只眼睛是冷的,空洞得像是没有尽头。别小诺每次见到这样的目光,便会下意识地低下头,忍不住想把自己藏起来。
树上的乌鸦嘎地叫了一声飞走了,把别小诺吓了一跳。在小镇,大家都把乌鸦的叫声当作是不祥之兆,这儿的人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别小诺发现,就连这里的猫也是不一样的。在小镇,经常能听见谁家的猫忽然无来由地叫了起来,喵喵喵地叫得人心里发慌。这里的猫却很少这样叫。而且它们几乎一点也不怕人,常常自顾自在路边徜徉着。在离别小诺几米远的地方,一只打理得十分干净的黑猫正懒洋洋地打着哈欠,别小诺蹲下身子想抚摸它一下,那只猫虽然紧张得翘起了尾巴,却依然慢悠悠地往前走。不远处一个老太太忽然一边鞠躬一边向别小诺说着什么。别小诺也没有听懂,只好脸上僵着笑停住了。
车站旁的那家弹子房里,总有许多人坐在里头。别小诺直到很久之后才知道他们是在赌博。但是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倒更像是在做某种不太有趣的游戏。别小诺曾在门口偷偷地观察过,到底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是怎么赌的。那大都是些看不出年岁的男人,偶尔也会有几个老太太夹杂在他们中间。别小诺看见里面的人大都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睛盯着面前的机器。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阵嘈杂的音乐声,把屋子里的一切都覆上了一层模糊暗淡的面纱。机器永远在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只能看见一只只弹子球沿着复杂而细小的轨道,消失在某个神秘的处所,又忽然一下子涌了出来。别小诺常常忍不住有些奇怪,这种并不新奇、看起来也没有多少乐趣的游戏,为什么会吸引他们,让他们乐此不疲呢?这让她很不理解。可是,这里总有那么多让人不解的事情,她也懒得探究其中的缘由。
每天到菜场买菜的时候,别小诺都要从那家叫エキゾチズム(异国情调)的小店前经过,别小诺一直不知道那个小店是做什么生意的。大多数时间,店门总是锁着的。直到傍晚的时候,才会有几个菲律宾女人把门打开。女人们穿着普通的衣裙,看起来甚至没有大街上的那些时髦女郎打扮得艳丽,只是身上的香水味很重。脸上化着淡妆,倒是打理得十分细致。大多数的时候她们似乎只是低着眉眼闲闲地坐在那里,偶尔抬起头娇媚地微笑着,那眼睛里却有种说不出来的勾人的魅惑,让人心中忍不住一动。有一次,别小诺看见一个刚从车站出来、提着黑色公文包的男人,被几个女人拥进了屋子里,小店的门随即被关上了。别小诺这才有些明白,这里是做什么生意的。
很快,周围便没什么秘密了。日子又像在小镇时一样,变得单调而漫长。森村依旧没有任何消息,别小诺曾给婚介所写信询问他的下落,却一直没有得到回音。而除了婚介所,别小诺也不知道应该向谁去打听这件事。这栋普通的公寓虽然住着人,大多数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座空房子似的。别小诺刚来的时候,因为孤独郁闷,又不知道森村去了哪里,曾经大哭过一次。别小诺一想到自己这么多年四处漂泊,现在好不容易把自己嫁了出去,却又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忍不住悲从中来。可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哭个痛快,便听见有人敲门。别小诺抹了把眼泪,红着眼圈过来开门。门口站着的那个中年男人先还虎着脸,怪别小诺打扰了他休息,现在见她的眼眶里包着泪,也不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便絮絮叨叨地和她说着什么。别小诺虽然没有听懂,却闻到了男人口中飘出的浓重的酒气。这让她忍不住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也不管是不是听得懂,只是连声说对不起。
隔壁的房间里,似乎住着一个老太太,总是像只影子似的栖息在屋子里。别小诺有时能听见老太太在屋子里放邓丽君的歌,这让她感觉十分亲切。偶尔出门的时候遇见,老太太总是客气地打着招呼。别小诺很想向她问问森村的情况。但是,无论她怎样搜肠刮肚,竟然想不起一个日语单词,说不出一个字来。面对老太太诧异的目光,她只能尴尬地微笑着。别小诺知道,在老太太看来,自己一定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或许,还是个哑巴。
不久,别小诺买了本地图册,开始试探着出远门。东京的交通发达是全世界都出名的,电车、地铁线路四通八达。车站、路口各式各样的标识都做得简明而实用,别小诺甚至不需要开口问路,便能在东京的大街小巷自如地往返。为了节省开支,除了车费,别小诺每天中午只是随便吃点面包、饭团之类的。累了,便在路边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那些大商店的门前,总有许多人站在那里抽烟。别小诺常常混在他们中间,眯缝着双眼,慵懒地注视着路边的行人。
一个女人在不远处揿灭了烟头,把背包里的录音机打开,坐在了地上。于是,诡异的音乐声便从女人的背包里流了出来。忽然,女人脱掉了鞋子,光着脚跟着音乐疯狂地跳了起来,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人群很快便自动围成了一个圆圈,于是女人便闭着眼,自顾自地舞了起来。女人已经不年轻了,有一张有烟瘾的人常有的那种暗淡无光的脸。穿一件浅灰色毛衣,身材纤瘦,看不出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是,痛苦和绝望却在一瞬间让女人的那张平淡无奇的脸一下子变得魅力十足起来。
女人的长发很快被汗水浸湿了,纠结在一起。别小诺能听见女人的喘息声,咻咻的,像是一只猫或者是别的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但是,女人似乎并不会跳舞,她的扭跳和旋转看起来倒更像是某种莫明其妙的疯狂。人群中很快便传出一阵轻微的嘲笑声,有人大声地叫着好。别小诺发现,就连女人的疯狂也像是某种程式化的东西。女人举起双手,仰面朝天地跪在那里,祈祷似地扭动着,然后便疯狂地旋转起来。猛然间又像晕死过去似的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等到大家开始怀疑是不是出什么事情的时候,女人忽然又一下子站了起来,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很快,警察便被招引了过来。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一边,还在犹豫着是不是要采取什么行动,原本一动不动躺着的女人却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别小诺十分奇怪,那个女人始终闭着眼睛,她是怎么发现警察的呢?警察似乎正在和女人说着什么,女人始终一声不吭,耷拉着眼皮坐在地上。女人从口袋里掏出张湿纸巾擦干净自己的脚,然后便穿好鞋子不动声色地收拾好背包离开了。
一旁的警察和围观的人群也相继散开了,周围很快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路上的行人依旧急匆匆地向前走,几个穿着夸张的广告衣、挂着广告牌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路口,看起来就像是个什么物件。一个面色疲惫的男人在向行人分发广告纸巾,几个抱着吉他、手拿铃鼓的年轻女孩正在远处唱歌,优美的和声在暮色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陌生的邀请。
周围到处都是陌生的景致,充斥着异国的繁华,但是别小诺反倒不像是对住处附近那样有兴趣了。身边走过的都是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那件枣红色棉袄脱掉之后,甚至没有人再多看她一眼。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别小诺谁也不认识,只有森村与她有些关系。但是,有时她觉得就连这一点也是不确定的,有点似是而非的样子。一想到森村,别小诺的眉头便忍不住皱了起来。
别小诺在东京很快便发现了许多中国人。在池袋北口,冷不丁地就会遇见几个讲中文的人。他们大都面色模糊,看起来匆忙而疲惫,别小诺也弄不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她曾试着和他们搭过话,可他们不是装着听不懂,就是支支吾吾地不肯多说什么。或者,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什么事?这倒让她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她还是喜欢到中国人开的商店里转悠。那些商店大都门面很小,货架上摆的东西都是以前熟悉的,虽然现在的价格翻了好几倍,她依然会挑那些便宜的小心地买上几样。手里捏着那些熟悉的小东西,走在陌生的大街上,别小诺觉得自己忽然凭空地多出了几分安全感。
离地铁出口不远的那家叫知音的中文书店,也是别小诺常去的地方。里头卖的差不多都是中文书,狭小的空间里杂乱地摆着各式各样的书报杂志。几个留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累了,手中的书扔在一边,席地坐着便打起了瞌睡。书店的服务员隔着老远,老实不客气地吆喝着,起来起来!不能在这里睡觉!这样的情景常常会让别小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家乡小镇。
别小诺还在一幢大楼的拐角处找到了一个中文网吧,有一架阴暗的扶梯直接通到四楼。推开网吧的门,里面的情形把她吓了一跳。二十几个平米的屋子里,挤挤挨挨地摆满了电脑。屋子里的光线很暗,大白天也开着灯。墙角堆着几只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鼓鼓囊囊的垃圾袋,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夹杂着一股方便面的奇怪的香味。屋子里的人大都在埋头打游戏,有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盒饭,也有人躺在椅子上蒙头大睡。
一个穿桔红色毛衣的男人正一边抽烟,一边谈笑风生着。别小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他在和身边的人说话,后来才发现,那人正和网上的什么人聊天。别小诺听见那人说,他住在二楼,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外面的一棵硕大的樱花树,窗前有一条狭窄的通向远方的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地方的路总是这么窄。有二辆汽车迎面开了过来,看起来几乎要撞上了。但是别担心,它们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便安全地让了过去。那个男人说,这个看起来有点平庸的地方其实有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富士见。之所以叫这么个名字,据说是因为从这里可以看见富士山。不过,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即便他睁大眼睛向远处看,依然什么也看不见。
男人说话的声音很大,但是网吧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对他说些什么感兴趣。别小诺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忍不住有些疑惑,他在和什么人聊天呢?是一个女人么?那个女人与他是什么关系?那么,她知不知道与她聊天的这个男人现在正坐在一个肮脏的网吧里呢?
一个男人闭着眼睛盘着双腿坐在椅子上,正跟着音乐在做什么隐秘的功法。一边双手合十,一边轻声地吟唱着。在离他不到半米远的地方,一个瘦弱的年轻男人正戴着耳机看A片。很快,年轻男人便离开座位,去了厕所。十分钟之后,那人又重新回到座位上,戴起了耳机。别小诺看见那人缩着脖子,微微地打着哆嗦,脸上还带着残存的激情与厌倦。
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并不关心别人。但是,别小诺从网吧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放在门口的雨伞不见了。第二天,当她再次去网吧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昨天刚办的一张上网卡上的钱已经全部用光了。网吧的管理员一脸茫然地看着她,说,这只能怪你的运气不好,我不知道怎么会出这种事。
每天清晨,别小诺总是早早地起床,和周围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急匆匆地向车站走去。清晨的电车上,到处都是人。车厢里却安静得出奇,只能听见偶尔的咳嗽声。有人低着头看报纸,也有人在手里把玩什么东西,更多的人只是一动一动地闭着眼打瞌睡。别小诺看见有人甚至一只手拉着扶手,也能沉沉地睡过去。有年轻女人正对着镜子抹口红,之后也像那些男人一样,闭着眼睛假寐。只是女人的双脚文雅地并拢着,手中的包也整齐地摆在膝盖上。
晚上,别小诺总是很晚才回家。但是,无论怎样晚,电车里依旧拥挤不堪。与清晨的电车相比,夜晚的电车总是弥漫着一股难言的躁动。喝得半醉的男人们摊手摊脚地睡着,晃动的头颅不时碰到身边的人。有人脸色绯红,独自微笑着。也有人站在电车出口处沉着脸凝视着窗外飞逝的夜景。一个男人忽然紧张地盯着自己的手表大声喊了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引来众人一片好奇的目光。很快,那个男人的身边便空出一块无人区。
只有电车报站的声音依旧那么礼貌周全、优雅动听,但是此刻听上去,却有点像催眠曲似的。别小诺闭着眼睛侧耳倾听着,很快便有了睡意。
终于到站了,别小诺随着人流向车站出口处走去。身边到处都是人,却听不见有人说话,耳边响起一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人群自觉地排成整齐的队伍,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隐秘的人在指挥着他们,一级级地朝着有光的地方走去。别小诺走在他们中间,常常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她想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别小诺发现,可以用世界上最伟大的字眼,也可以用最恐怖的词汇来形容她身边的这些人。可是,无论是伟大还是恐怖,却都是与自己无关的。而且,对于身边的这些人来说,她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国新娘而已,而且,就连她的新娘身份也有些让人生疑。或许,她早已经被那个有名无实的丈夫抛弃了也未可知。虽然她还不能确定,但这却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她现在在周围人的眼中就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名目的莫明其妙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谁会在乎她,又有谁会在意她的感觉呢?
于是,那种巨大而空洞的、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又慢慢浮了上来。别小诺忍不住有些诧异,她原以为自己一离开小镇,就等于是把过去抛在了身后。别小诺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去的一切就像是她后背上的那颗黑痣,早已经变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它们步履敏捷,精力旺盛,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早已悄悄尾随着她,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在她还在左顾右盼、彷徨不知所措的时候,它们早已在不远处等着她,嘴角挂着微笑,眼中蓄满倦怠,一副悠然自得、胜券在握的模样。
难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么?
别小诺发觉,自己从小到大似乎就从没有爱过谁,也没有被什么人爱过。就连父母,别小诺也不太能确定,他们是不是曾经宠爱过自己。等到长大成人之后,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让她刻骨铭心过。那几个曾经与别小诺关系亲密的男人,都像是初春微凉的寒风,刮过之后便永远消失了。别小诺虽然也曾伤心失望、痛哭流涕过,其实心里并没有多少痛苦和怨艾。现在,有时她甚至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在别小诺的记忆中,他们早已与那些逝去的岁月混杂在一起,变成了灰色背景上一个个模糊不清的斑点,闪烁着卑微暗淡的光泽。只有许多年前的巫加越,偶尔还会在她的梦中出现。当年那些蚀骨的羞辱经过岁月的稀释之后,早已经消失殆尽,只留下一点若有若无的淡漠。别小诺坐在午后的阳光下,冷淡地回想着当时的种种细节,就好像是在回忆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在那些独自回忆往事的日子里,别小诺忽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以前一直以为是巫加越改变了她,别小诺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这其实只是个误会。别小诺发觉,即便当年没有巫加越,她的人生也早已经注定了。她永远也无法像小镇的姑娘们那样,安静知足地生活。不是她不能,而是她根本就不愿意。在离家出走的那些年,别小诺其实有过许多次机会,把自己的生活安置好,是她自己主动放弃了。虽然后来也有过后悔的时候,但是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还是会犹豫着。而机会就在她的犹豫中悄悄远去了。有时,连别小诺自己也有些不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而且,这样的犹豫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看起来,一切几乎有点像是个陷井。她的出走、拒绝和等待,只是意味着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陷井——嫁给从未露面的森村,继续让自己堕入不可知的无用的混沌之中,继续着与往日相同的难耐的等待。
别小诺正坐在上野公园的湖边长椅上低着头想心事,忽然听见有人在她身后说话。开始的时候,她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可是,那人就在她耳边说话,而且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别小诺转过脸去,看见有个年轻的黑人站在自己身后,正指着面前的不忍池中的水鸟,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别小诺摇了摇头,向那个黑人笑了笑,结结巴巴地说,すみません、わたしは日本語が少ししかできません(对不起,我只会一点儿日语)。别小诺原以为那人应该转身离开了。可是,他却在椅子的另一端坐了下来。
黑人有时说日语,有时说英语,为了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还夹杂着连续不断的手势。那人告诉别小诺,他叫杰森,是个美国人,在东京的一家电气公司上班,业余时间喜欢打游戏和看电影。那人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可是别小诺却大都没有听明白。别小诺一点也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又为什么要和她说这些呢?忽然,那人凑近了些,又说了一句什么。那人离得实在太近了,这让她觉得很不习惯。别小诺把身体往后退了退,谁知那人却不依不饶,又凑近了过来,还殷勤地伸出手,帮她捉衣服上的毛絮絮。别小诺这才发现,自己早晨新换的黑色风衣上,竟然有这么多的毛絮絮。这让她有些不好意思了,忍不住说了声谢谢!
那人抬起头冲着别小诺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然后继续勤勉地捉起了毛絮絮。刚捉完一个,又发现了下一个,于是赶紧再去捉。他的动作让别小诺觉得十分滑稽有趣,脸上不觉露出了笑容。那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于是又凑近了些,问,どちらに住んでいるの(你住在哪里)?这一次,别小诺总算听懂了。她局促地笑了笑,说了一个地名。那人犹豫了一下,说,遠いけど、今から出かければ間に合うと思うけど(太远了,不过要是我们现在出发的话,还来得及)。说完,便站起身挽起了别小诺的手。
别小诺这才意识到,他一定是误会她了,把她当成是一个需要温暖和慰藉的寂寞女人,或者是一个妓女。这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在电影院里陪陌生男人看电影时的经历,忍不住有些羞惭起来。
那时候,在电影院的包厢里,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女人。包厢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交易就在包厢里的那张柔软的紫色长椅上秘密进行着。黑暗中,陌生男人熟练地解开别小诺的胸罩,然后便在胸脯上粗暴地揉捏着。坚硬粗糙的手指就像是个理所当然的入侵者,千军万马般地一路横扫过来。有时,陌生男人还会有些特殊的要求,但总是会被别小诺十分坚决地拒绝。好在电影很快就放完了,等电影院里的灯光再次打开的时候,黑暗中的一切便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暴露出灰败不堪的本来面目。别小诺这才注意到,陌生男人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拎着一只脏兮兮的旧旅行袋,脸上满是奔波劳顿的疲倦。别小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身上的那件连衣裙已经穿了好几天了,看起来有些脏。由于睡眠不足,一脸的暗淡与憔悴。陌生男人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切,匆匆丢下几张钞票,便头也不回地一路远去了。
别小诺忽然觉得有些厌倦起来,推开那个年轻黑人的手,说了声对不起,便径直站起身离开了。别小诺原以为,这次有些奇怪的遭遇就这样结束了。可是,第二天当她在傍晚再次来到上野公园时,却发现那个年轻黑人正坐在昨天的那张长椅上。看见别小诺,那人连忙站起身冲着她笑了笑。然后向长椅的另一边挪了挪身体,意思是让她坐下。
别小诺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那人告诉她,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还以为她不来了呢。那人又絮絮叨叨地说了一些别的什么,别小诺也没怎么听明白,只是点点头答应着,心里却有些温暖的潮湿慢慢地浮了上来。别小诺低着头看面前的湖水,暗绿色的湖水在夕阳中幽幽地闪着光,里面模糊地印着两个人的影子。别小诺睁大眼睛看水中自己变了形的脸。那是一张略有些扁圆的脸,皮肤很白,二只眼睛不大,却是弯弯的。头发蓬着,遮没了大半个脑袋。像是知道自己不好看,本能地想要藏起来似的。别小诺一点也弄不明白,那人到底看中了她什么呢?她身上穿的还是当初从小镇带出来的衣服,简直不像样子。鼓鼓囊囊的暗红色防寒服,腋下和袖口都已经磨得有些发白了。现在已经是春天了,要不是傍晚还有些冷,这身衣服肯定就有点穿不住了。
那人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对别小诺说,“日本語を勉強したいなら、教えてあげるけど”(你要是想学日语的话,我倒是可以教你)。别小诺点点头,顺从地跟着他一句句地念着。书上的假名和汉字,都是她以前就认识的。那人却不知情,只当是自己教得好或是别小诺太聪明,脸上忍不住露出些惊异和喜悦。别小诺很想告诉他,这些以前自己都在小镇的那个日语老师那里学过。可是自己的日语词汇太过贫乏,无法表达情楚。于是,只是抬起头笑了笑。
下一次,那人便丢开书,只是漫无目的地聊着。别小诺很快便爱上了这样的闲聊。开始的时候,她还感觉有些吃力,但很快便应对自如了。原本对别小诺来说生涩无趣的日语,在交谈中日渐变得温婉美丽起来。就像是在笼子里关了很久的鸽子,搭拉着翅膀,浑身落满了灰尘,原以为早已经不会飞了。没想到一出笼子,却忽喇喇一路飞了出去,只留下几根翻飞的羽毛。
那人似乎也喜欢这样的约会。每天傍晚总是早早在湖边等着,直到天黑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时,两人也会一起吃晚饭。也大都是在附近吃些面条、咖喱饭之类的,而且都是各自付帐。那人没有抢着付钱,这让别小诺觉着安心了许多。终于有一天,那人跟着别小诺一起上了电车。她开始的时候还以为他有什么事恰好与自己顺路,也就没有多追问。等到那人和自己一同下了车,别小诺这才感觉有些不对。
两人肩并肩地向前走,谁也没有说话。别小诺忽然凭空地有些紧张,四处张望着。这些天来,与这个年轻黑人在一起时,别小诺从没有想到过森村,可是现在,照片上那个瘦瘦的穿西装的男人忽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别小诺忽然觉得,或许森村就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她做的一切事都瞒不了他。这让她顿时有些不安起来。别小诺也顾不得礼貌了,只是说了声不行,推开那人的手便开始往前跑。
别小诺原以为他会追上来的,可是,他并没有追。别小诺的脚步不由放慢了,心里忽然变得空落落的。她低着头慢慢地向前走,能感觉到远处年轻黑人的目光十分困惑地落在她的后背上。不知怎么,别小诺的心里忽然生出几分不舍,忍不住有些怜惜起来。一件才刚刚开始的事,谁也说不清它会如何向前发展,便被她毫不留情地连根拔起。难道她连这点柔弱得可怜的温情也承受不起么?那个年轻的黑人长得很好看,结实挺拔的身材,有一双柔和漂亮的黑眼睛。而且,他还是个十分风趣、很有意思的人。别小诺一点也不讨厌他,不仅不讨厌,甚至有些喜欢。她知道他需要她,可是,难道她不需要他么?和他在一起,别小诺不是没想过。可是,总觉着不太可能。因为太愉快,时时刻刻都像是离别一样。现在,别小诺能感觉到他怀中那片温暖的空虚,她真的恨不得立刻去填满它。
别小诺停下脚步,转过脸去。她很想回去找他。可是,身后已经没有动静了。那人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别小诺叹了口气。这样也好,那么,她就不需要再后悔什么了。